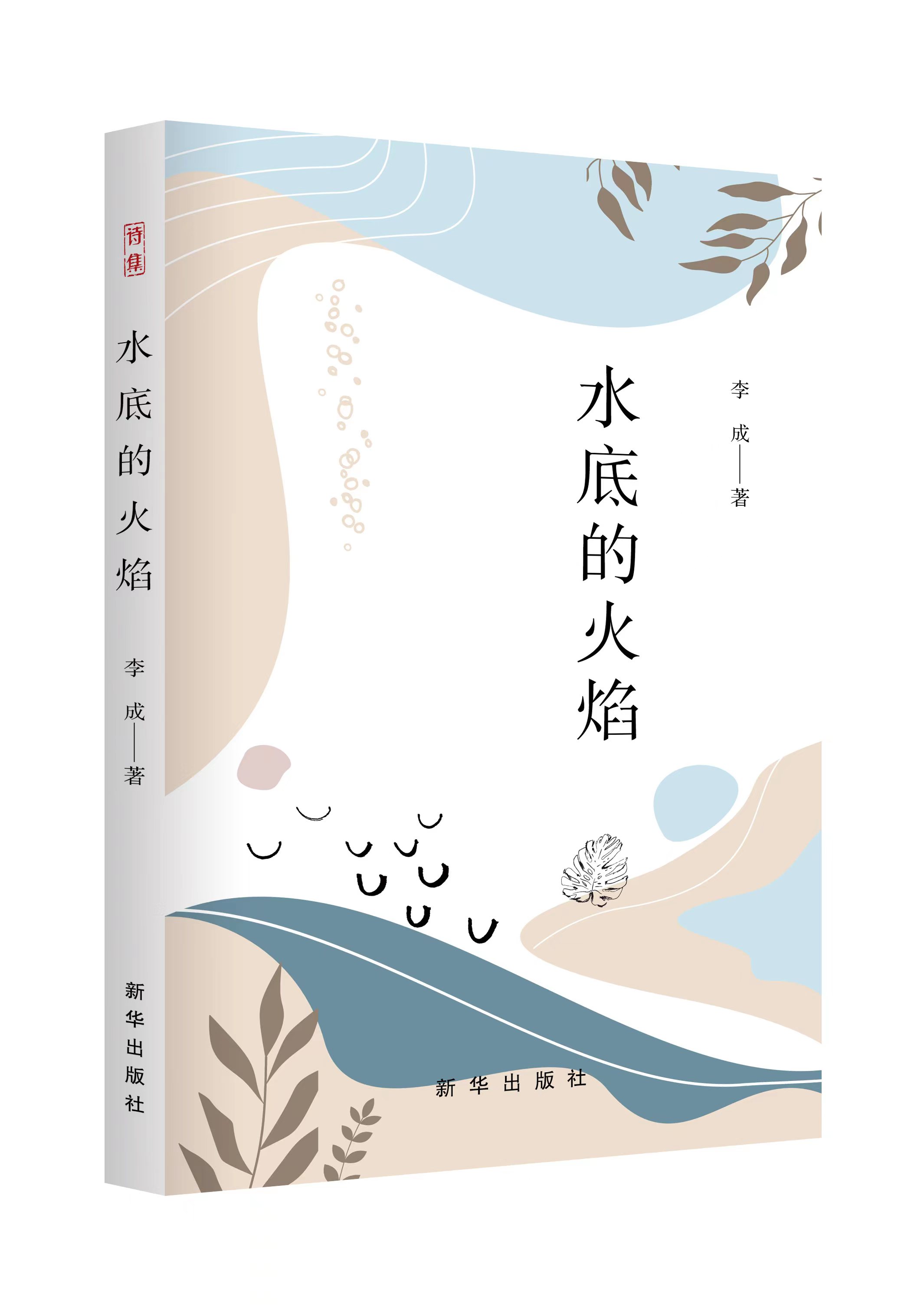“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这是雷平阳在《亲人》一诗中毫不掩饰地宣扬自己对家乡的热爱。这样的偏执其实是许多人的偏执,不失率真和性情,有别于另一些人在后工业化时代路口的患得患失,乃至于无节操的反叛。虽然《亲人》一诗并没有归入《云南记》,但这本诗集无疑是《亲人》内脉和气息的接续,更是其宏旨和意趣的夸张和集大成。关于乡土、崇敬和挚爱的主题,雷平阳实在是欲罢不能,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基于其上反复吟咏、表抒,才使自己好似有归宿感。
《云南记》共四卷,分别为《蓝》《流淌》《隐身术》《尘土》,辑录诗人2006年至2009年间约153首诗歌。按诗人自序中所言:“近几年,我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生活里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比如父亲西游。这就使得我在此期间写下的诗作,总是绕不开山水、密林、寺庙、虫鸣、父亲、墓地、疼痛和敬畏等等一些‘关键词’”。诚如斯言,诗集中的作品像一批行星总在相应的轨迹上运动,统领它们的似乎便是诗人自以为的关键性词语。但细心阅读便会发现,指引或干脆说“命令”诗人因循般写作的,不如说是乡愁或乡土情结(但不能简单将之归纳为“乡土诗歌”), 因为雷平阳还说过:“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连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一个写作者虽跟普通人一般存活,安身于物质搭建的框格里,其实精神上有赖于文字的抚慰,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诗人们的确更容易焦躁、抑郁、不由自己。幸运的是,他们用文字把自己喂养,雷平阳就是这样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雷平阳还拥有丰饶广袤、地貌复杂、风情万种的云南。
从卷一《蓝》开始,雷平阳的每一口呼吸、每一次心跳都与云南大地息息相关(相信此前是这样,其后也是这样)。整部诗集就是云南的浓缩和翻版,可以想象诗人优雅地在故乡大地上踯躅俯仰,流连、品评、感伤,从而慢慢将自己内心里的热爱具体化,并不断获得克服失忆症的有效方法。在《德钦县的天空下》,诗人“像一个乡下木匠,建起了神殿”;在《奔丧途中》,他感慨“一个世界终于平静下来”;在《边疆》,他总结出“人类的蚂蚁,荡着秋千。像猴子捞月亮”;在《易武山顶》,诗人“内心的秘密,被天边涌动而来的开阔,堵回了肺腑”……在杰卓山、昆明西山道、楚雄和高黎贡山上,在怒江、昭鲁大河、红河之畔,在拉祜族、基诺族、傣族居住区,诗人决绝地行进,他的诗集简直就是一幅路线图,他要用文字再造出一个云南,一个仅供自己独享和朝拜的云南!
在自建的“诗歌云南”里,诗人不单单是宽泛、机械地漫游,所过之处,均能由表及里地触碰到这块厚土的主脉和律动,由仪态万方的物象找寻到人性和神性秘密的交集点,从而将自己心灵深处的抵牾渐渐剔清,洗礼般地,一次次脱胎换骨,“一次次受领阅历的吊诡和文字的甜蜜”:
修一条铁路,在自己的身体内
让火车在上面,缓缓行驶
……
这列火车,我没有用它
运输过什么,就一个人坐在上面
只求被它拉着,把体内的景点跑完
(《铁路》)
寨子有一颗心脏,众神在那儿放声歌唱
人们躬身而来,净身,献上牺牲
匍匐在地,洗耳恭听,然后领命而去
(《爱伲山寨速写》)
终于想清楚了:我的心
是土做的。我的骨骼和肺腑,也是土
(《尘土》)
《云南记》并不以意象取胜,多用小说句式入诗:“与万迪恒、朱绍章诸君/醉酒于楚雄州街头。/浅风。/明月”,“下午四点,天空蔚蓝/一群海鸥,越往高,越细小”,“我爱过一个女子,她在/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在一个国家/不断加厚的历史书里/呼天抢地,哭倒了长城”。诸如此类,多为批评家诟病。事实上某种文体的进化是不可遏止的,有与其它文体模糊边界的倾向,诗歌是,散文、小说何尝不是?雷平阳作诗的小说笔法还是与其诗歌内容相契合的,是诗歌化的小说笔法,不喧宾夺主又开合有致。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内敛而克制的叙事风格,才使其诗歌更饱满、更有气力。读者沉浸其间难以自拔,一定被拨动了心弦——每个读书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琴吧!艾略特说过,“诗歌是比散文更接近生活的一种文体”,大约便是此意。
与其说我们感动于雷平阳的诗歌,不如说我们桎梏于物欲的性灵假以其手得以抒发——我们在行色匆匆之余终于可以稍息环顾,原来我们忽略和遗失的有很多:热爱、伤怀、眷念、悲恸,包括触景生情。难怪评论家霍俊明说:“雷平阳诗歌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物象、器皿和空间。”
诗人张执浩曾对雷平阳说:“你还有故乡,我只剩下故居。”雷平阳用文字再筑故乡,等同于替我们再筑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