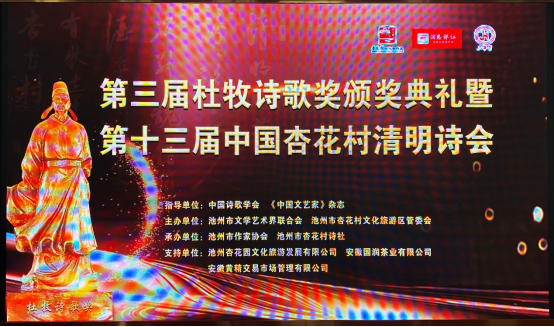过了知天命之年,依然与诗歌相遇,到底是一件幸运的事吧?李成读诗,写诗,保有诗歌在心里,出版《水底的火焰》——这“第一次得到发售机会的诗集”,令他振奋。他用诗歌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那一份感知,对于生活的那一种热爱。
每一朵花都犹如梦境
每一朵花都带着夙世的心情
悄悄地爆出一个芽
前不久枯枝还像一根铁棍
就像小孩子扒着门缝
闪着眼睛微凸着嘴唇
哗啦一声大门就开了
泻下一地阳光如黄金
……
人生过半,沧桑历尽,周遭的美好依然深深触动诗人的心,空气中,流溢着春天的消息。
这些诗歌陡然间亦将我唤回到诗歌的年代,唤回到如诗的年华,唤回到有诗相伴的岁月,刹那间我有一些恍惚——蓦然回望,我不知道今日的我离诗歌,已经有多远多久了。诗歌,出现在现实消隐的地方呢,还是心灵所在的原初之地?而今天的我,去到了哪里?
恍惚间,诗人李成也有过瞬间的迷茫和感伤,他在诗里问:“那个写诗的孩子去了哪里?/怎么无影无踪?”
我与李成曾有过一个简短的电话,当我说送他几本某社重点打造的作品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当下,我只读外国文学作品,其他书以后再说。”彼时的我会心一笑,知道他是图书编辑,而他对书,原本有着很高的期待。每天接触书,他对书有别样的感觉吗?在诗歌《我的藏书》里,他袒露了一点自己的心迹:
……
任何文字都是画图
它们跟我一样
用一堆废话
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执着
我曾带着它们跨过时间之轴
像宝贝一样生怕蒙尘
彼此像故友主仆甚至
手足 如今失去水分似的
它们 像一堆落叶
唤起不了我的兴趣
我感觉陌生日甚一日
彼此可有可无
生活才是一本大书
常读常新而这么多藏书
越来越与我格格不入!
生活在前,书籍在后。或许,读了几十年书的李成早已经过了迷信书籍的年龄吧?然而诗歌,依然被他钟情。他在现实的喧闹中努力辟出一片小天地,让诗歌进来,让生命温润,让自我,回到最本初的模样。以至真至纯的情意,他写下《大地与花》:
大地上的语言无声地涌动
每一朵花都那么朴素
因为大地就这么朴素
那是源自诗人心底的朴素吧?
大地是他的书房,在那阔大的承载里,他任意驰骋。
但我要的是一间
流动的书房早晨
它安在一条河流的岸边
明亮的河水顿时大涨
中午应该在一棵树下
每一片叶子都有清香
夜晚则是长满石头的山腰
每一块石头都开始熠熠闪光
……
无论是在巴黎隐秘的一角
还是在大西洋上
浪花簇拥的小岛
时光在翻着书页 书页在翻着时光
诗人的语言总是清新明亮。在草原,“蒙古长调就是穿过天空的河流/一盏盏油灯点亮/一只只小船顺流而下”,“每一棵草都将燃烧”。而当夜色四合,“穹庐从四面八方围拥/每一株小草却都波澜不惊。”在洗砚池边的大树旁,诗人看到,“洗砚池边树被秋风一吹/叶子变成漫天/狂草的诗章……”
有时候,诗歌又如补足现实的幻想,而诗人是不羁的。李成说:“我要开一所诗歌银行/让每一个公民都从这里/获得想要的力量!”诗歌是诗人的呓语吗?在这里,理想与现实彼此打量。现实越是逼仄,人类就越需要诗歌,就越需要不泯的诗心吧?
李成说他是自然之子,他要回归家园。在诗中,他表达自我与自然、与万物的切近联结,道出“我是人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人有什么了不起
我曾经捣毁野蜂的家
我还打死过蛇踩死过蚂蚁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厌恶
现在我感到羞愧
我愿意向它们道歉
我穿着树叶裙
它们一定会把我接纳
齐物之心,使他的诗歌平和舒缓,超脱超然。
在诗中,他写海风、落日,写万家灯火,写石头剪刀布,写太阳照着丘垄;在诗中,他感叹不变的命运和代代的传承……
他以诗歌存在,他在诗歌中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