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加班文化盛行”等痛点问题,《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的举措,通过强化执行监督来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知名企业通过赶人、断电关灯等手段“强制下班”,一度登上热搜。
我们已然生活在“效率崇拜”的时代。从前说竞争激烈是“过独木桥”,如今是“拼赛道”,独木桥毕竟要靠走的,赛道则自带速度感;从前表述时间是“抽几根烟的功夫”,如今说“一天刷不了几个视频就没了”;从前羡慕富翁海边悠闲晒太阳,如今赞叹像王健林这样的商业大佬超人般作息时间表,普通打工人有“休假羞耻感”……
雍正曾经赞誉张廷玉的办事效率:“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及也”。三百年过去,即便是普通人效率也已大大提高。然而,技术突飞猛进、工具机器更新换代,社会却不是多年前的预测那样——“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反倒是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不仅是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飞驰电掣地与时间赛跑,就连孩子也失去双休,忙得要在两个培训班的有限空档里找时间吃饭。
紧张、焦虑、抑郁,成为社会年轻一代的普遍情绪心态,对此,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王德峰在B站一段访谈中谈到,这是人被异化的突出表现。他认为,哲学上现代性绝非褒义词,现代性病症的核心就是异化和进步强制。为效率而牺牲自己作为人的自由时间,“这是个重大的代价”。学者熊培云在著作《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中亦不无痛心地说道,人已沦为“技术迭代的附庸与效率链条中的一环”,甚至可能成为“无意义的数字尘埃”。
如果一天24小时里面20个小时是为了存活,剩余时间用来获取生活资料的话,王德峰叹“就没有任何文明可能了”。如果一切都服从于效率,就连教育也屈服于算法,首当其冲就是人构建意义的能力的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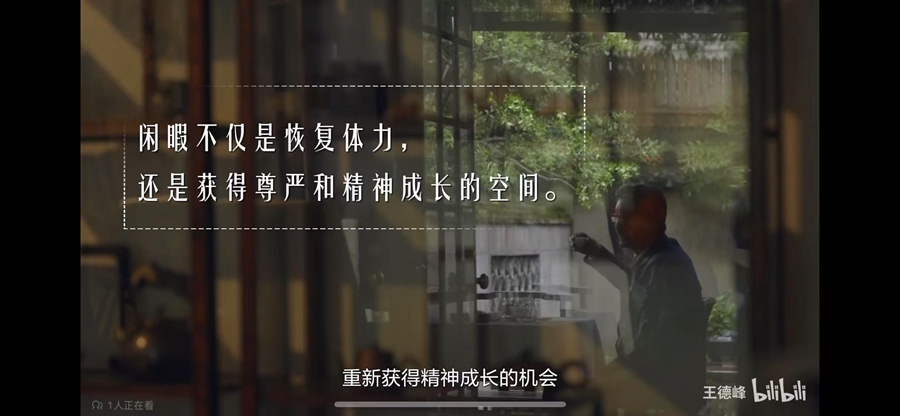
视频截图
效率是为了带来闲暇。闲暇是为了丰满精神世界、构建意义世界,获得创新创造的可能性。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王德峰解释道:“闲暇不能仅仅消极地理解为恢复体力,要重新回到人性的尊严中去,重新获得精神成长的机会。”因为人类只有在闲暇时间中,才有可能发展作为人类的能力。
设计师、诗人、工匠威廉·莫里斯在著作《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中写道,“有价值的工作给我们带来如下期望:在休息中享受到快乐,在使用这种工作的产品时享受到快乐,在每天的创造性技能中体验到快乐”。

视频截图
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如何改变时刻紧绷的状态、守护个人闲暇时间和精神世界,王德峰说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法律上捍卫我们的闲暇时间的权利。这和《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的“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等举措指向一致。第二,有效利用闲暇时间,将其转变为精神成长和能力发展的空间,它与提升工作能力无关,没有任何功利性,比如过文艺的生活,绘画、作曲、写诗等,“人需要这种精神生活”。
“你不能穿着拖鞋在屋子里漫步,在外面散步,你能创造什么呢?”如果一味服从于效率、崇拜追逐功利性目标,社会又何谈创新精神呢?(小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