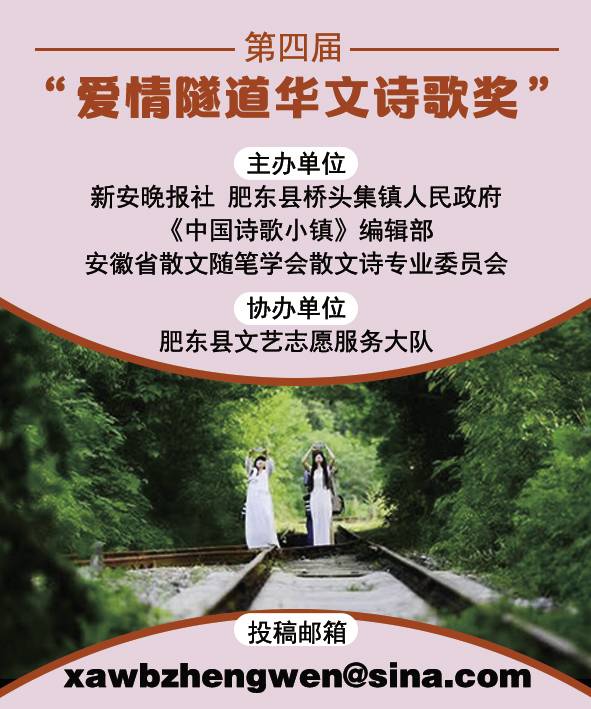月光是夜行客,不经主人的同意,就大大咧咧地穿过阳台落地窗,斜斜地铺向客厅木地板。于是,阳台上,客厅大半截木地板上,像洒了层霜,粉白粉白的。
客厅与厨房、卫生间窗户对开,夜风夹着丝丝凉气,穿室而过。雨后的夏日,月华如洗。只要不是特别闷热,我都不开空调,抱一床竹席,睡在客厅靠近阳台的木地板上。如水的月光,透着一股凉气洇进来。凉气蒸腾,我感觉木地板上似乎袅着一层薄雾,轻如丝绸,爽滑柔顺地盖在我身上。睡在如水的月光里,心静自然凉。睡梦中,我坐上了一弯月牙船,潜回遥远的故乡。
故乡是一卷老胶片,那些人,那些物,那轮皎洁的月亮,在胶片里显影,重现,鲜活。
太阳还没有落山,母亲便将门前的空场打扫一番,泼上凉水降温。天色渐暗,我和哥哥将竹榻、凉床、竹席搬出来,摆在空地上。父亲砍一把黄荆,或者野蓼、青蒿,夹在稻草中点燃,摆在空场周围熏蚊虫。一家人在竹榻、凉床上吃过晚饭,一轮明月已挂上了树梢,刚才还是鸡鸣牛哞的村庄渐渐安静下来,枝头的鸟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蛰伏在草丛里的虫子活跃起来,唧唧唧地低吟浅唱;青蛙在池塘里敲着鼓点,放大了村庄的幽静。
月夜是白天的延续,却比白天清凉。庄子里的大人带着被单,坐在平铺于门前的凉席上,摇着芭蕉扇,聊些农事。我和小伙伴们忙着扑流萤,玩累了,就躺在竹榻上,看夜空中的人造卫星一明一灭,看最亮的星星一闪一眨,遥想天外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又藏着哪些秘密。父亲和母亲忙完了家务,各端一条板凳坐在我们身边,拿着蒲扇为我们赶蚊子。在扇子的“啪哒”声中,父亲给我们讲二十四节气的来历,讲怎样看云识天气;母亲给我们讲述牛郎织女的传说,讲《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比我读书早的哥哥为我指认天上的北斗、银河,讲彩虹是怎样形成的、人造卫星是怎样上了天;姐姐指着月亮上的斑点,为我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梦见自己成了一只大鸟,飞上蓝天,飞上月球。醒来后,四周寂静,但扇子的“啪哒”声不时在耳边响起。此后很多年,只要想起故乡的夏夜,我的耳畔依然响起家人为我讲述故事和科学知识时的涓涓细语,响起母亲为我摇扇驱蚊的“啪哒”之声。
我喜欢在月夜露宿纳凉,喜欢月夜里的故事传说,喜欢月夜里的科技启蒙。故乡的那些夏夜,月色溶溶,星河点点,如水的月光如水银泻地,给田野、山峦、村庄、树林披上了一层银辉。暴晒了一天、热闹了一天的村庄,在月光中漂去暑气、躁气,渐渐沉淀下来。仿佛被月光淘洗过一般,我感到自己浑身通透澄明,内心宁静,无比惬意和轻松。
那是故乡的夏夜,有如水的月光,有蛙鸣萤舞,有地气升腾的清凉,还有淳朴的乡情乡韵,如诗如画。月光如水,清凉一片,照亮了我的梦乡,也装饰了我的童年。
此后,我离开了故乡。许多年过去,父亲和母亲相继走进了泥土,兄弟姐妹陆续离开故乡,漂到儿女所在的城市,帮忙带孙子孙女,助儿女一臂之力。老家没有了亲人居住,大门紧闭,于我而言,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如一壶老酒,温在如水的月光里,在城市阳台上的某个难眠之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好在,还有高悬于夜空中皎洁的明月。它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家的客厅,照亮了兄弟姐妹所在城市的阳台,也照亮了故乡青葱的草木和蛙鼓虫吟。离开故乡的姐妹弟兄,还有那些游子,虽不能时时见面,但我们拥有同一轮月亮。举头望明月,望见你我他,也望见故乡,望出许多况味来。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又不是原来的月亮了。
城里的夏夜无处纳凉,无处沐浴如水的月光,难以遥望远方的故乡。这,是不是我潜意识里喜欢睡在月光里的缘由呢?
楼下不知谁家的电视里隐约传来那首《城里的月光》,歌词唱道:每颗心上某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白塔河夕照 吴国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