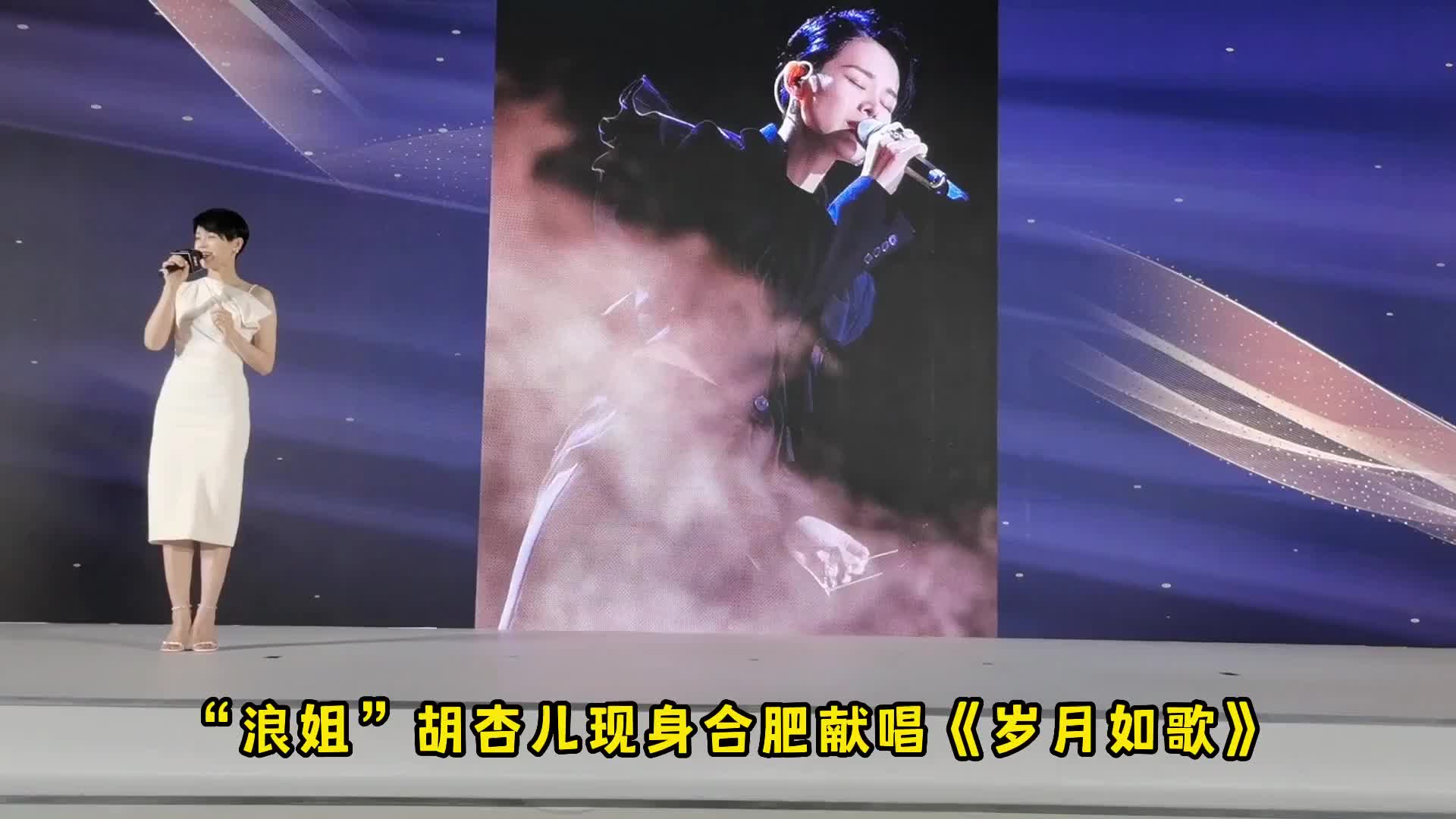豆腐屋还在老地方,看见它,我总想起一些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原先的披厦太小,施展不开,父亲想扩大作坊,于是新建了这爿豆腐屋。与原先相比,虽仍显简陋,但高大宽敞多了,人走进去不压抑。屋里砌了大锅灶,添置了两台机器,还摆有长长的案板和压榨架,冲浆缸置于屋中央,人行其间,还宽绰有余。
当曙色微明,夜色还在飘荡,豆腐屋已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父亲忙着捞豆、洗豆、筛浆、冲浆,母亲则帮衬烧锅。那时烧柴,需专门一个人添柴。寂静的清晨,这些声音如温暖的晨曲。
天刚放亮,豆腐屋就热闹起来,如小集市。村民来买豆制品了,有豆干、豆渣、水豆腐、豆腐皮等,品种很丰富,交易声、说笑声、脚步声,如交响曲。我们也被唤起来帮忙,因为母亲要回家烧饭。我们如堂倌跑来跑去,我负责出售,妹妹负责烧锅,姐姐则在父亲后面帮忙。喧嚣的场面一直要持续到上午九、十点钟,才慢慢如潮退却。
其实豆腐屋的主角是父亲,我们都是“跑龙套”的,因为他出身豆腐世家,一手掌握着豆制品的全部制作过程,从捞洗黄豆开始,然后是筛浆、冲浆、点卤、压榨,我们都插不上手,也无法插手,那是技术活。作坊器物也都是父亲自己打制的,木工活和瓦工活全揽了,宛如怀揣十八般武艺的人,其实为成本计,自己开店哪有闲钱雇请别人?父亲边琢磨边打制,倒也像模像样,制作出来的豆制品周正、光亮。那座竖有三四米高烟囱的大锅灶至今还在,巍然矗立。
做豆腐是重活,苦、脏、累俱全,取巧不得,光是担水,一天就要担几十担,那时可没有自来水,一拧自个哗哗淌,全凭肩担脚跑。白日沟沟坎坎看得清楚,脚步准确;晚上则全凭感觉,踏空、扭脚都很正常。豆浆烧开都是滚烫的,捞豆皮要贴着水面,冲浆桶粗圆,可装六七十斤水,父亲两手拎着,难免泼洒,但父亲忍着。还有冬天,水冰冷刺骨,但父亲徒手在水里捞豆、洗豆。父亲沉默寡言,再多的苦累也不吭一声。一次夜间劈柴,不知劳累还是疏忽,一斧劈在脚背,一下现出骨头,但父亲忍着剧痛,包扎后继续忙碌。
父亲的豆腐屋很出名,沿河两岸的村民都来采购,以致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如今和村民谈起,他们仍会说到父亲的豆腐坊,豆腐怎样怎样,这让我感到欣慰和温暖。
如今豆腐坊关闭了,父亲也走了,但豆腐屋还在,虽然岁月痕迹很重,墙皮剥落,窗棂豁缺,里面机器也被拆走、搬空了,但我每每看到豆腐屋,依稀的往事还是涌来,宛如岁月未曾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