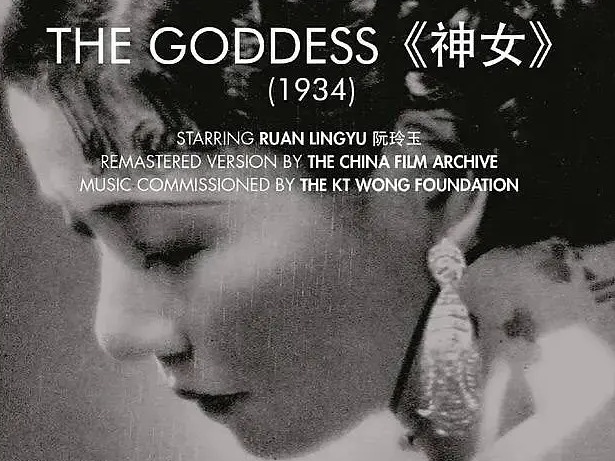不久前,我回了趟故乡。
打开尘封的老宅,堂心的正壁上那幅《松鹤延年》的中堂还在,那张虽然陈旧但古意犹存的八仙桌还在,就连八仙桌上那只绘着《采樵归来图》,上着白釉的大茶壶也还在,那三只已经豁了口的茶盅,就像三个板头儿子那样,孝顺地簇拥在大茶壶边。此时,抬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母亲遗像,笑微微地仿佛对我说:“儿啊,走累了吧?喝一盅大壶茶吧!”
过去,在我们皖南小山村,再怎么穷,待客也有一壶大壶茶。这壶有陶壶,瓷壶,最不济的也有瓦壶或竹壶,茶叶当然没有谷雨尖。最好的茶叶自家不舍得喝,母亲都拿到集市上去换盐换油了。待到春茶采到二、三茬之后,最后的一茬“粗枝大叶”,才轮到自家人喝。不过,乡下人没有那么斯文与讲究,口渴了,甚至等不及将茶水倒进杯子里,直接捧起茶壶,仰起脖子一顿牛饮,那个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喝琼浆玉液还要过瘾。
每天早上鸡还没有叫,母亲就悄悄起来了,挑水、洗菜、烧饭、泡大壶茶是她必做的早课。边烧山泉水,边洗大茶壶,等到汤锅里的水沸了,母亲揩干双手,敏捷地在大铁桶中捻起茶叶,或一些她平时采制的草草棒棒,放进大茶壶中,倒些沸水进去,先醒;不到半袋烟的工夫,再倒一些沸水进去,又润;此时,再把大茶壶的沸水灌满,再泡。等到我起床吃饭上学时,母亲便把一盏黄澄澄、酽冽冽、香喷喷的大壶茶,轻轻地放在我手边。我一口气喝下这盏茶,这一天,干什么事精气神都旺盛得很。
我家大壶茶的内容,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从小生长在大山中的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大山就是敞开的教科书,大山也是无私的聚宝盆。母亲上山砍柴、下田劳作之余,山上的山楂果、野菊花、覆盆子、金银花等都成了母亲的囊中之物,田埂上的桑葚子、霜桑叶、车前草、马齿苋等也都是母亲的眼中珍宝。细心的母亲把这些采摘回来,清洗晒干,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不同的大铁桶内。春节期间,因为母亲在茶中掺了山楂果等,家里人并没有因为暂时的暴饮暴食而导致胃不舒服;夏天双抢时节,因为母亲在茶中放了野菊花、金银花、马齿苋等,家里人没有中过暑,更没有生过疖子。
母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村里不管谁家有困难,她都鼎力相助,常常是一盏热茶、一碗热饭、一腔暖语,甚至一卷她捏着出汗的辛苦钱。当年,我家的火桶一年四季都盛着火。火桶里,搁着母亲准备的家常饭菜;火桶中间,放着母亲泡好的大壶茶。母亲出门干活时,家中的钥匙就醒目地挂在大门上,门锁成了一个摆设。左邻右舍的人渴了或饿了,都可以进屋吃碗饭,喝盏水,就像到自己家中一样平常自如。放学之后,我放下书包最先扑向的也是这只火桶,看到火桶中有饭无菜时,我就用大壶茶泡饭,味道竟是那样香。
如今,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30多年了,我也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吃过不少大小名吃,现在回味起来,我还是最难忘母亲的大壶茶泡饭,那个滋味绵长啊,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贴切的形容词。那只一年四季都盛着火的火桶,不仅当年温暖了我及不少村人的胃,也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让我在人生最寒冷的季节,心,总是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