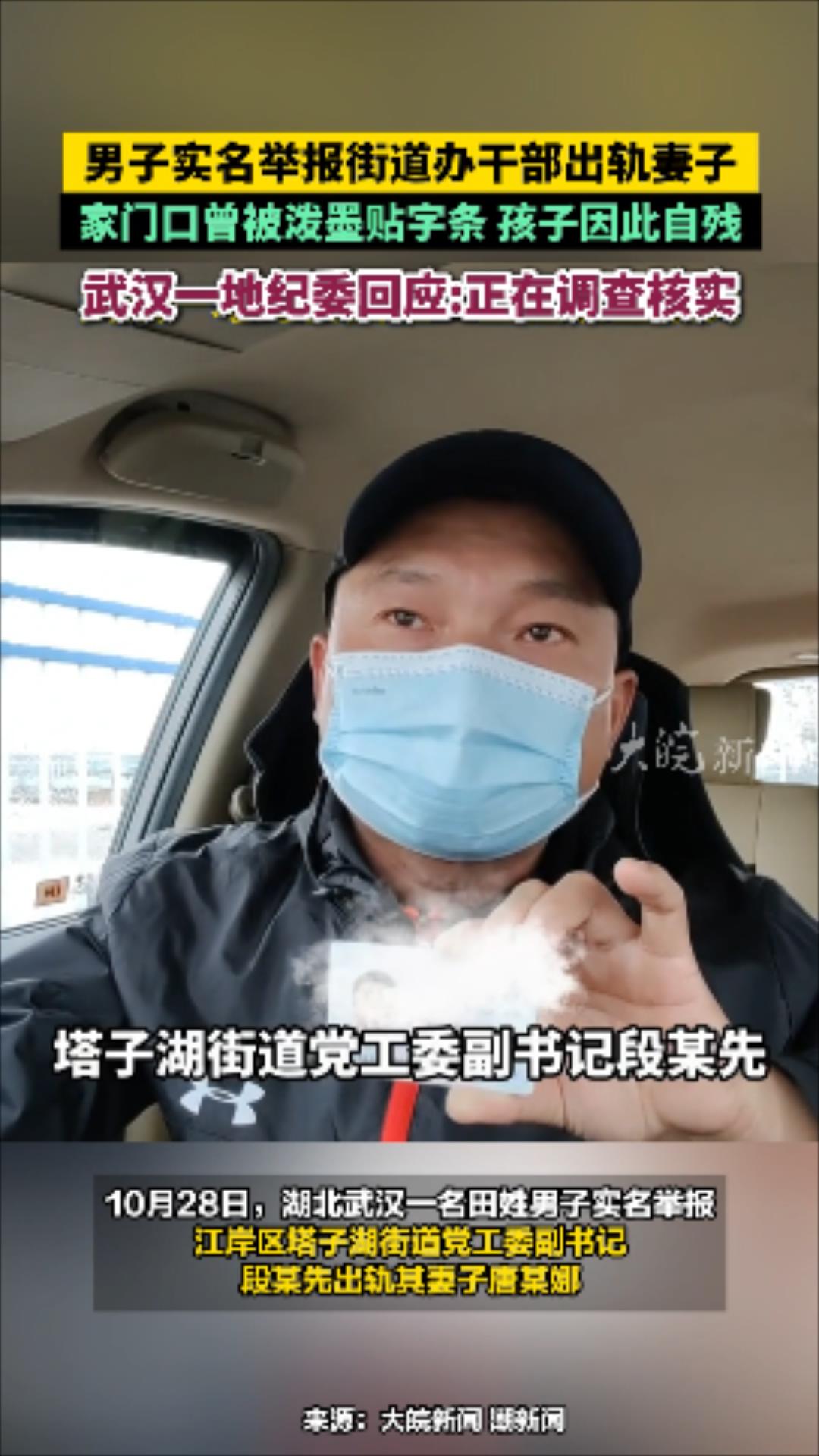在今天的阅读体系中,诗,正在沦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精神容器。对诗和诗人来说,我倒觉得这远非一种坏事,诗就应当去艰难之地呼吸,在不被理解中迈开步子,走到更丰富的人群中去,扩展接受面,诗人不能仅仅与同类特质的人形成共振。诗应去更抗拒它的人群中,在完全不能预测的时空中,在一种普遍性的麻木与艰难中,活下去。似乎惟有这样的命运,才能诞生伟大的诗歌、诗人。
循地理
昨天下午我从合肥到黄岩,近四个小时的高铁,穿过江淮丘陵、巢湖湿地、沿江圩垸、皖南山地、杭嘉湖平原,到达浙东山区。人在旅行中,暂时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惯性轨道,空间的快速切换,时时刺激着感觉系统的更新、呼应,并与之进行微妙互动,人在逼近一种纯粹的语言生活。在我看来,旅行中所获,其实是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奇妙叠加。
古往今来,好诗、耐读之诗、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经典之诗,多是在行旅之中写成的。越是艰难困顿的行进,好诗就越多。无论是李白的《蜀道难》《秋浦歌》,还是杜甫的《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等;无论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流放之途,还是苏轼一再被贬之路,都是他们的灵思大放异彩之时。
车经宣城,想到诗本有着强悍的命名能力,此城三处胜迹“谢朓楼”“敬亭山”“桃花潭”,全是被诗命名,或者是被诗再造了,清除了原有形象,生成了全新的内在。《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李白平生仅见的两首为底层贫民写的诗,都写于这附近,“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直白深情,摧人肝肠。
车经杭州,想到一条大河,上游在安徽境内叫新安江,中游由皖入浙叫富春江,下游澎湃入海叫钱塘江,一水三名,各有其丰厚的信息埋藏,江河在自然演进中包含的天道物理,和一个大诗人在少年、壮年、暮年的精神气象之变也大致类同,值得细细揣摩。
车经绍兴,忽想到“新文化运动”三位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故乡竟都在这条线路上;近天台山时,想起佛教中国化的两大流派,禅宗与天台宗,诞生在这条线路的一首一尾附近。
这一路上,每一个村名、镇名、县名,山名、水名,都仿佛一扇小小的语言之门,后面连接着更幽深的空间。诗不直接源于景象的“看不尽”,而源于人对“每一寻常物每一个名字竟然都不可穷尽”这一现象的震惊,源于时时想“破门而入”的渴望,也源于从名、物向“某种内在”的不可止息的冥思与行进。
许多诗人擅于此道——循地理入诗、时空并置,以放大诗中的距离感,拓展它的结构性空间,让地名之上附着的复杂滋味,也参与语义的生成。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中用了四个地名,前句隐含了剧烈起伏的动荡感和风急浪高的不确定性,在后句中,则感受到两个城池之名构建的墙郭稳固、安身立命气息。苏轼写“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地在当年,都是偏僻蛮荒之处,又相距遥遥,他绝口不提杭州这种曾泛舟吟唱、常醉忘归之地,倒将这三个困窘的地名并列,充溢着“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的命运荒寒之感。
人的行进伴随着语言的行进,好诗中往往蕴藉一种“没有尽头的动感”,它命令自己不要在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上形成终结。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有两句诗:“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冰雪闪耀何其寂静,下句中迅疾的减退与消融,在外表遮蔽下有一种奇妙的速度与完成,很传神。上大学时,我读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有一幅画面至今镌刻脑中,有一首诗写坠落时,“大地迎面,刷的一下直立了起来”。我写挂在墙上一幅静物画,画中枯树仍在继续枯去。“对生而言,死只是其背面,而枯才是一种登临”,将一种已然止息的东西,在语言中继续它不竭的行进,这种行进,对诗而言,是一种发现。
见语言
发现力,是诗的核心。但“发现”不是知识,诗恰是将此知识化为生命力的一种觉醒。刚才我一直在讲各种“见”,见,即相遇,人的感知系统与世界的触碰、连接、贯通。下面我从另外的维度拆解四个层面的“见”。
见天地。各眼见各花,各有各的见法。杜甫24岁时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帕斯卡则凝神于一根芦苇;詹姆斯·赖特写道:“如果一步跨到自己体外,我将开成一朵花”,而王阳明却说:“心外无物”。世上并无这朵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写作者不断观察、探向外部世界,也姿态生动地为他的“小世界”命名。阮籍叫它“竹林”、卡夫卡叫它“城堡”、马尔克斯叫它“马孔多小镇”、奈保尔叫它“米格尔大街”、莫言叫它“高密东北乡”……我没有资格混入他们这个行列,但我有自己清晰的命名:“黑池坝”。这种命名永不止息,拆穿了,其实是无尽的生命旷野中同一个炽烈的地址。
见自我。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很容易伪饰自我,或者说,沉溺于一个自塑之我,被那个形象所感动,陷入自我怜悯,甚至是茫然不自知的自欺之中。我读到一个大画匠将自己喻为“坐在沙漠中的斯芬克斯”,“伟大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我听得笑了,这个形象和这个说法,不是一种真实的“自我”之境,不仅不是他的,也悖离了所有人的自我。在写作中,我们应当去见一个真切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一人分饰多角的、在撕裂中又渴望统一的自我。看清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光影交织的自我,而不是修饰的、伪装的、与自我分离的一个替身。佩索阿一生用了60多个化名、异名,甚至在报纸同一版面以不同名字在激烈分歧中争吵,也就是说,佩索阿体内至少有60多个裂变的他自己。自我是一个人的内在现实,我很难想象一个活在边疆大漠的诗人,与一个活在江南水乡的诗人,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如此迥异,却要写出心理结构与语言气质高度类同的诗歌,不幸的是,此乃当前诗歌生态的一个切面。
见众生。按桑塔格的观点,在旁观、注视、进入无边的“他者之痛”中,建立语言通道,让自身生命逐渐浑厚起来。“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写“三吏三别”时的杜甫,有了这种深刻的“觉他能力”,相对于过往的、在语言中达成自觉的杜甫来说,他是刚刚挣断了某种绞索的新人。唐代李绅年轻时写《悯农》,“汗滴禾下土”,坐了大司空的高位之后,纸醉金迷骄奢无度,刘禹锡受邀赴他的家宴之后,写下“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刘禹锡之“断肠”,是因为头顶永悬着“他者之苦”。世代如此,底层悲歌往往有人唱而无人听,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倾听者,有一双从群体亢奋情绪中完全冷却下来的耳朵,能从异常静默中听见内在的喧嚣,或者正相反。但“觉他”不是对众人的盲从,不是求得最大音量的附和。有时候,万头攒动恰是另一种形式的荒漠。
当然,此“三见”只是种粗率的分类,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更多时候它们是叠加与混溶的。而在此之中形成某种融通之后,就会生出“见语言”。语言不是词语,不是语法,不是修辞,它是一种覆盖性、统摄性的力量,特朗斯特罗姆说,词是雪原上清晰、偶然的蹄印,而语言正是茫茫雪原。
我们每个诗人,都要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语调、节奏、语言方式,来确立内在声音的个人性,最终令此声音摆脱短促与混乱,成为语言旷野上一种悠长的、甚至是恒久的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