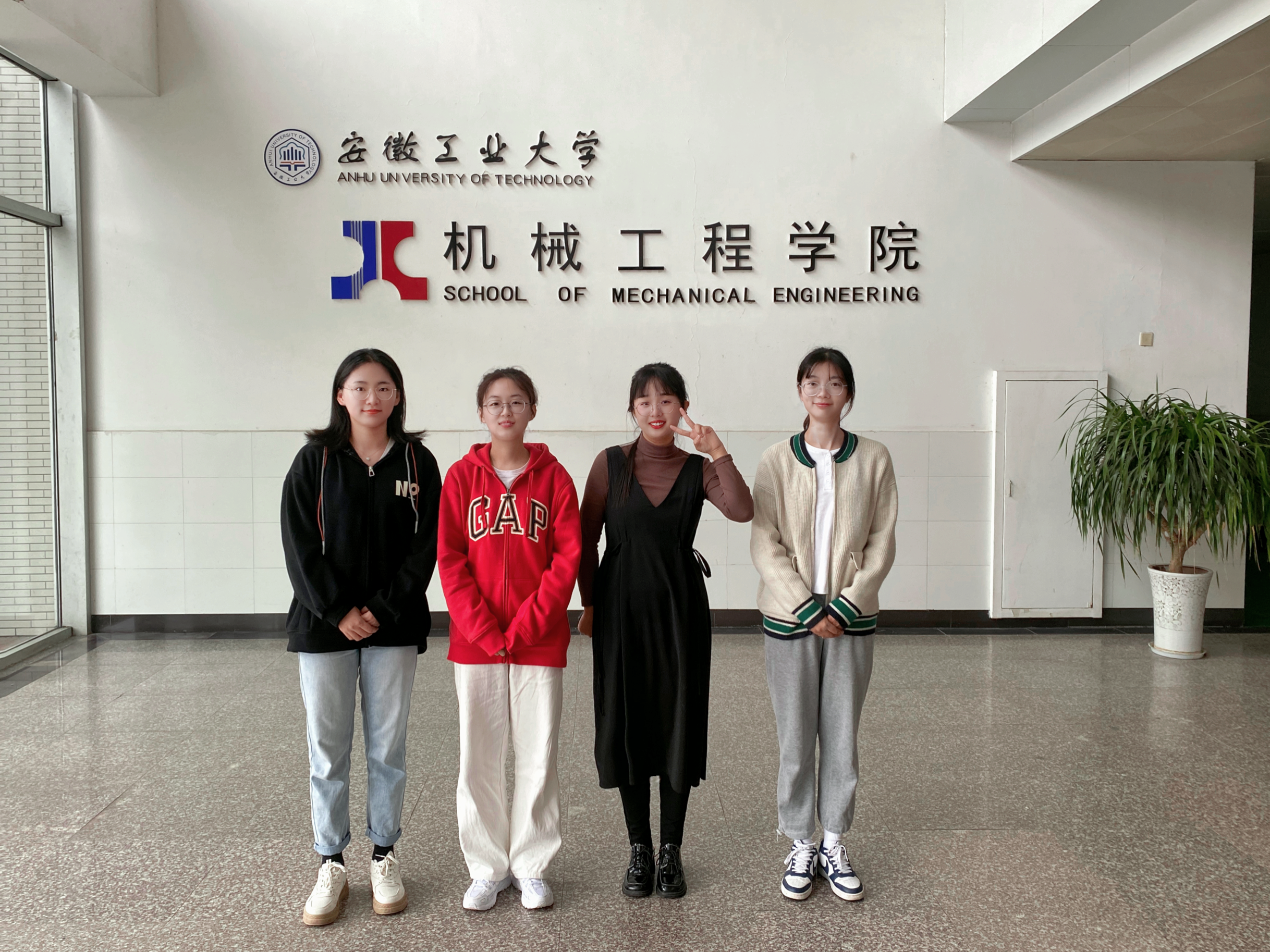自豪
一九九五年果压枝头的九月,我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跟着父亲跨进了合肥工业大学的校门。当时,雄伟的主楼正在改造,办理入学的地点便设在了主楼前,八九张桌子一字排开,跟摆摊似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神圣的殿堂,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进去呢?也不应该被轻易地打扰。在空旷的主楼前,抖落掉一身的尘埃,平静一下躁动的内心,然后再坐入殿堂,才不失尊敬吧。
在一排桌子前,我正在张望,一位长相清秀的小姐姐(后来得知是大四的学姐)热情地接待了我,让兴奋中夹杂着不安的我,有一种到了新家的感觉,一颗心瞬间踏实下来。学姐领着我在人群中穿梭,在一张桌子前办理好手续后,又来到另一张桌子前,不厌其烦地引导着我,有时候还帮我填表格、拎东西。
九月,阳光依然毒辣,汗水顺着学姐的秀发直往下滴,父亲不停地说着“谢谢”。很快,我便交了伙食费、住宿费、学杂费,领了棉被、饭卡、洗脸盆,办好了一切手续,该去宿舍整理床铺了,想向学姐道谢,可话到嗓子眼又咽了下去,觉得这样的感激“轻”了点,在我发愣的当儿,学姐冲我挥挥手,消失在了人群中。
校园内的水泥道路很有灵性,两旁的法国梧桐也非常的可亲,仿佛在哪儿见过。风吹树叶的哗哗声,像欢迎我到来的掌声,伴了我一路。路的上方,不到百米便会出现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有的写着:“欢迎您,未来的工程师”;有的写着:“欢迎您,未来的计算机专家!”在一条横幅前我和父亲都停住了脚步,上面写着“欢迎您,未来的厂长经理!”条幅的右下角署名是“管理系宣”,我一看,便乐了,当时便不由自主地整了整衣领,生怕别人说我不像厂长的样子。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娃儿,看见了么,是你们“管理系”(管理学院在当时还是管理系)写的呢,说你们要大有作为喽!父亲说完便哈哈大笑,那笑声很响,二十多年过去了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失落
在20世纪90年代,能考上大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上了合工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显得非常了不得。在很多学生的羡慕目光中,一些学生,包括我,都把大学当成了人生路中的一个“巅峰”,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攀爬,到了“巅峰”便想歇歇脚喘口气,全没了初中、高中时代拼搏的劲头。我以为上大学,就像走走过场,是件很快活很轻松的事情。只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听下课,课后不做题,也不复习。结果,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便两门“挂科”——高数和历史都不及格。
当补考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我的父母没当回事,觉得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我却难过极了,甚至还有点不相信,以前相当优秀的我,怎么会沦落到补考这般地步呢?我不服,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当别人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我不得不又捧起了高数和历史书本。
大一的第二学期,我开始重新审视“大学”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学习阶段,明白了它不是人生路上的“巅峰”,而是“半山腰”,我还必须继续奋斗。早上,我不再睡懒觉;晚上,也不再去工大西门的宁国路上看录像,双休日,也不再和宿舍的室友们斗地主……图书馆里,有了我的身影,斛兵塘边,响起了我朗朗的读书声。我之所以这样下功夫,希望能“王者归来”,还像高中一样成为班级中的尖子生。
可是,大学里强手如林,每个学生都是高中学校的尖子生,我苦干了一年过后,成绩依旧平平,特别不堪的是,在大二的下学期,我的英语成绩以2分之差再次补考。忧伤如水,彻底地覆没了我,无边无际无可解脱。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枯坐在斛兵塘边,痴痴地发愣。
一天晚上,在宿舍快要熄灯的时候,睡在我对面上铺的尤良安同学,捧着一本书慢悠悠地说:“当你因为没有鞋穿而哭泣的时候,想想那些失去双脚的人。”他或许是读着玩的,也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故意读给我听。当时,我像遭电击了一般,浑身一阵颤抖。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想想那些成绩比我还差的人,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我又是多么幸福啊!自己尽力了,赶不上别人,也没什么遗憾的,大学里本来就高手如云,把自己当作天鹅里的一只丑小鸭,不就行了吗?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脸上浮现了久违的笑容。我已经很久没有这般开心地笑了。
幸福
把自己定位为“丑小鸭”后,心中突然就放松了许多,但我并没有放纵自己。大学里的晚自习,没人监督,学习全靠自觉,我开始跟着室友尤良安去阅览室看书。遇到高数上的难题,也虚心向班中的同学请教。到了大二下学期,我才感觉真正适应了大学的生活。我不再敏感、自卑,开始参加班级和校园的各种活动,开始和同学们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听姚禄仕老师给我们讲会计,我感觉就是一种享受。虽然,他讲课带着浓重的桐城口音,但我们都能听懂,并且领悟得很透彻。他就像对待小学生一样,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一遍一遍地讲,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神都不再迷茫。
晚上,听室友唱歌,也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室友们都买了播放机和英语磁带,在晚上熄灯前,他们便装上歌曲磁带学唱歌。沈先春来自安庆,他唱起歌来颇有黄梅戏的韵味,细腻动人,辗转缠绵,只是老跑调;我很佩服李青松的勇气,他唱歌根本就没有调,但他就是敢唱,声音大得像吵架一般。我第一听他唱歌是心惊肉跳,后来习惯了,觉得非常好玩,蒙着被子在被窝里偷偷地笑,常常笑到肚子疼。
现在想来,我还觉得很有成就感的是,睡我对面床铺的秦科,买东西要我陪他去,去食堂打饭也要我陪他去,我以为他是和我对脾气,后来才弄明白,他是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出宿舍,显然,当时的他,把略微有点肌肉的我当成了他的保护神!
日子如流水般静静地滑着,一转眼四年就过去了,大学过得很平淡,没拿过奖学金,但也顺利地取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丑小鸭嘛,就这点理想。
怀念
毕业以后,每次受到委屈,我就能想到我的母校合工大,就像受了伤的孩子会想起母亲一样。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到周末,我就去工大的食堂吃饭,咀嚼工大的味道,咀嚼在工大读书时的幸福时光。后来,工作忙了,便去得少了。
去年的三月份,我有事去合工大。校园里的学生真是不少,他们有说有笑地从我身边走过,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看向我,我感觉自己就像幽灵一样,在校园内四处游荡。校园内的梧桐依旧,路两旁的一草一木,似乎和以前并无两样,可它们都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在它们面前停下,它们却自顾自地在春风中舞动。
我来到管理学院楼,想哪一间教室我曾经学习过;我来到斛兵塘边,想哪一块湖边的石头我曾经坐过;最后,我来到了9号楼116宿舍的窗外,望向曾属于我的小小床铺,睡在我曾经睡过的床铺上的一名胖乎乎的男孩正在读英语,看我看他,放下书问道:“叔叔,您找谁啊?”我想回答,可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赶紧转过脸去,泪水扑簌簌直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