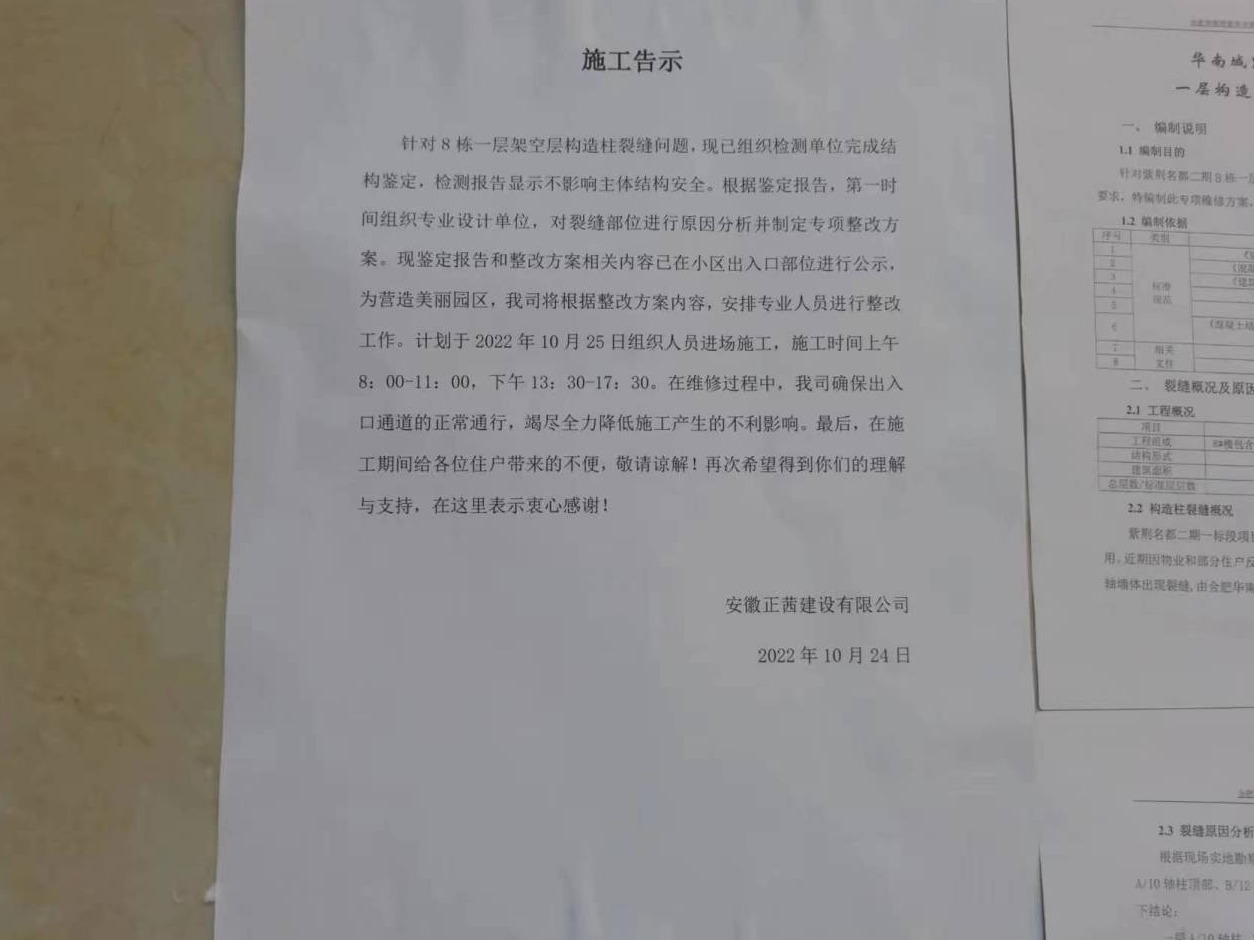一些年里乡村借事繁杂,日子不好过,借借还还如草荣草枯,一茬接一茬。
借事简单,锹锨锄头,转个身子,到左邻右舍就可借得,用完再转身还了,一桩借事就完成了。招唤可打,可不打。升米、瓢面也是常借的,“浅升借米满升还”,家家户户遵守。
乡村的炊烟陆陆续续,或浓或淡或厚或薄,可没见断过。借得轻松平常,还得硬朗明白,乡村多得是和美的气韵。
乡村的借事,还是有讲究的,约定俗成,比如“借米不借柴,借衣不借鞋”,口口相传,有道理,也有顾忌。米永远可借,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皇帝还不打饿兵呢。家中断顿,提着升子走上一趟,村陌多意,村人也不松泛,多走几家,总不会空手回的。柴火就不一样了,到处有的,树枝、荒草、牛粪,都是烧锅料。借柴火的人,肯定是个懒汉,借了,助懒汉的懒劲。“柴”和“财”还谐音,谁愿把财气借出去呢?至于鞋子不借,也是有说法的,赤着脚多不碍事,何况草鞋都会编,凑合下就过去了。若借了,不小心穿破了,“破鞋”和破衣裳不同,破鞋有指向,说不上的别扭。“鞋子”还谐音“孩子”,虎毒不食子,再穷的家也不愿把“孩子”借与人。
乡村的道理浅显,顾忌中也约定了美好。
不过,借事从来就不是不可突破的。村子里的柱子,就什么都能借得。柱子是孤儿,七岁那年死了父母,算是吃百家饭的,守在父母丢下的三间草房里挨日脚。他什么不借呢?柴米油盐,衣帽鞋袜,实际上柱子不需张口的,村子里东家西家南家北家,但凡能从牙缝抠出的都会送上门去的。柱子知好歹,远远地道声谢,近近地说,借的,一定还。柱子在村子里活了下来,筋筋道道的,还算有点朝气。
村子里最大的借事是借钱。
米、面、菜、油是自产的,钱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一个村子里没活头钱,转了一圈又转回来,急得直跺脚。好在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终还是借到了。
乡村为借钱找了个词,叫“掇”钱,显得郑重,“掇”有文化,比“借”文气。借钱时说得也婉转,说,这几天手头急,掇两个,十天半月就还。不提钱字,但也都知是钱的事。“掇”字有意思,“拾掇”常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上有段子:“那周四不时的来,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冲撞;些小借掇,勉强应承。”此处的“借掇”暧昧,没有乡村的“掇”明快。
乡村的借事正大光明,又被一句话固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掇了钱,说好了磅了肥猪还。放心,猪上了磅,钱还没焐热,人还没到家,钱先还上了。借钱也没有打条据一说,一句话撂下,板上钉钉子,人不死债不烂,何况还有父债子还顶着。
和借事沾边的事,还有“行”,比如饿了“行口饭吃”,渴了“行口水喝”,路走黑到边了“行个歇”,等等。行的事是不需还的,与借与掇有关联,也有区别。不过总体上都是行个方便,与人方便也就是与己方便。“好事逼人来,天与行方便,红裙情愿配袈裟,不待旁人劝。”村里人把行事做得顺溜,模样周周正正。
邻村发生的借事更大。大刚子家出大事,几间草房遭了火灾烧个精光,八十岁老父亲一口气没上来,去世了。大刚一夜急白头,老父的丧事无处办。村子里不止一家伸直了颈子,去他家办。大刚感激涕零,在邻家设灵堂,光光鲜鲜为父亲办了丧事。几个老人抹着大胡子说话:“宁借屋停丧,不借屋成双。”死者为大,也算救急。“屋成双”是指给人做新房的,这房子不借。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如此的借事,让人感动。
柱子长大成人了,外出闯荡,三十年后,柱子回村,一家家送上的红包沉甸甸的,村子人集体拒绝,但仍像过节样,户户请,家家接,柱子又吃了次百家饭。柱子含泪离村,不久为村子修了条路,路叫百家路,也算好借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