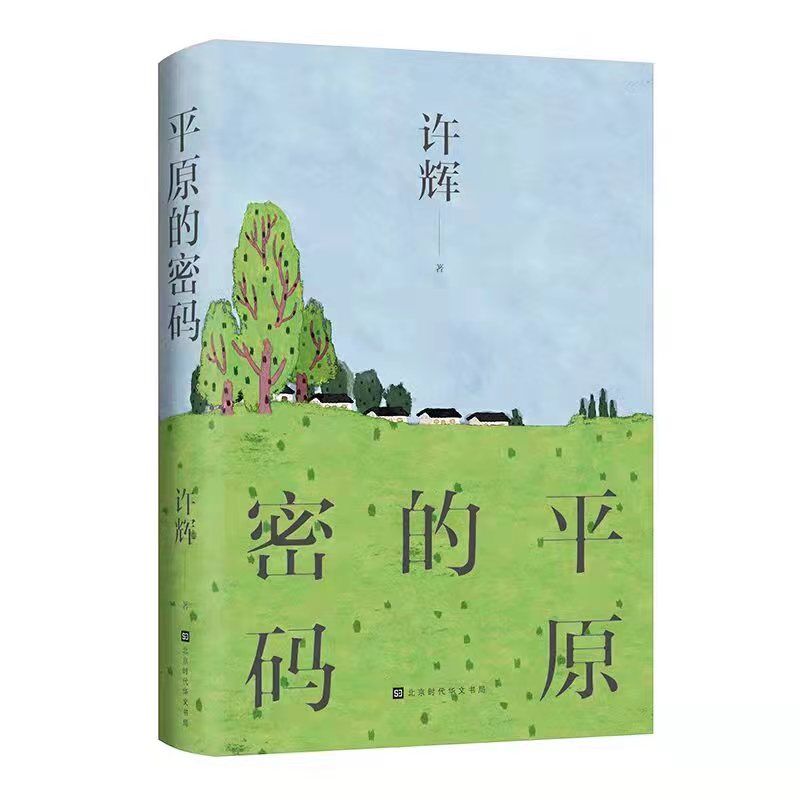有一篇评论文章称:读当代小说,读了十万字,还没听到一声鸟鸣,也没看到一片树叶;还有评论称:不知从何时开始,植物成了当代文学天地里的稀有物种。作为一个读者和草木爱好者,我深以为然。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不能一概而论。
我书架上就有一本2012年出版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作者是阿来,据说是他相关博客的结集。这是我读过的阿来唯一的一本书,因为书中记述了他在成都拍摄、观察植物的经历与感受,与我的爱好相契合。阿来以小说家名世,2010年的一场病,拉近了他与草木的距离。入院时病房楼下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蜡梅;手术后,相隔十来天,蜡梅竟成了迟暮美人,只剩下几缕幽香,在寒风中浮动。正是这一树蜡梅,在冥冥中引领着阿来,让他的目光,暂时从书卷中移开,投向身边的草木。他说:“我将它们一一拍下,回去检索资料,看它们在植物学上的意义,以前的文人怎么描绘它们,然后书写植物花事。”这件事成了他重要的日常作业,无论到哪里,草木都是他的追寻对象。有一次他去了意大利,带回来几百张照片,其中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他找来《植物志》一一辨认,确认一种,就把它发到微博上,与人分享,也让自己高兴一阵子。单就这一点,他和我们这些草木爱好者,算得上是同好,但放到作家群体中,就显得比别人技高一筹了。
我家里还有另一本叫《植物记》的书,作者李汉荣,是个写散文的。我长期订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杂志,自己偶而也在该杂志上发点短文。我在这本杂志上常常读到李汉荣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写他家乡的花花草草的,他的这本书,也是《散文》杂志策划出版的。李汉荣与阿来不同,他一边看着草,一边想着诗:“这泛绿的青草可是从白居易的诗里生长出来?”“我看见了车前草,还是在《诗经》里那么优美地摇曳着。”“看韭菜排列得那么整齐,像杜甫的五律……”李汉荣的文字,充满了奇思妙想,读来很是赏心悦目。而李汉荣自己,却是一本正经,他认为世上没有虚伪的植物,没有邪恶的植物,没有懒惰的植物。“与植物呆在一起,人会变得诚实、善良、温柔并懂得知恩必报。”
诸多小说的环境书写中,也会语涉草木,但通常是作为背景素材,像绘画中的大写意,或一笔带过,或恣意挥洒,但认真的写作者并非如此。2002年我在西安,下了班就读《白鹿原》,有一天读到第三章,白、鹿两家换地,这坱地与鹿家原有的地隔着一垅埂,那埂上长着野艾、马鞭草、菅草、薄荷、三棱子草、节儿草、旱长虫草(牛筋草)等七种草。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一个疑问:这是泛泛之笔呢?或是实写?便托人引我去拜访陈忠实。只见他爽朗一笑:老程,不如你抽空去白鹿原看看。到了双休日,我真的让司机陪我去了那里,按书中给出的方位,在灞河滩靠西的一侧搜索。因为是秋季,除了书中那七种野草之外,还拍了好几种其它草木的图片,脑海中的疑问至此便烟消云散了。回来的路上我想,这就是大师与众不同之处吧。
安徽的许辉,前几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人人都爱在水边》,书中总共出现九十三种草木,可谓树木琳琅,芳草萋萋,其中以芦苇、楮树、油菜、小麦、灰灰菜、扁豆、牛筋草、荠菜、毛谷谷草(狗尾巴草)、荷花、蒲草等亮相最为频繁。许辉笔下的草木,没有奇花瑶草,都是自然界里草根中的草根。许辉在书出版之前,曾当面向安农大一位植物学博士讨教,请他为自己笔下的草木,作技术层面上的把关,这种做法,这样的精神,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当然并不止上述几位,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就被公认为是从庄稼地、从荒野中冒出来的文字。翻阅他们的书,我往往分不清书页里生长的,究竟是一点一横长的文字,抑或是一花一世界的草木。作为一个读者,每每让我心旌摇曳。
世界太坚硬,草木软人心;万事有套路,花草自纯真。所以我要说,倘若草木不在场,无论什么样的文字,也感动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