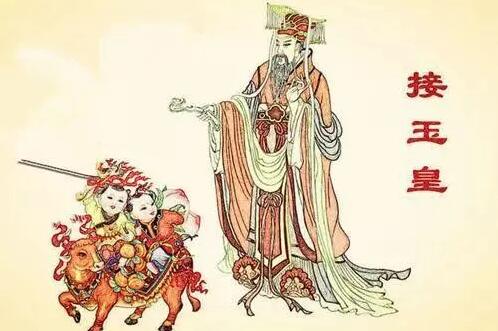儿时,最喜欢给家里买红糖了。村东头有个小店,离家不远,穿过塘埂和几条田沟就到了。
说是小店,其实也就零零碎碎地摆上一些物件,上上下下的木柜子摆放着一些家用品,但最多的还是酱油、醋、盐、糖、香烟之类。那个年代,乡亲们都不富裕,也没有闲钱置办其他家当。“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
店主是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的样子,带着一副断了腿的眼镜,只在边缘用丝线缠绕着,这在当时乡村是少见的。男人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和和气气的。晴天,常看见他在门前散步、晃悠;阴雨天气,他就靠在柜台里的座椅上,眯着眼看报纸。听说,他是外乡人。他很少主动同顾客搭讪,说真的,他真不像个生意人。
“称一斤红糖……”我怯生生地说着,将捏出汗的五角钱摊平,放在柜台上。见他没动静,我朝里面巴望着,怀疑他是睡着了。我探出脑袋,踮起脚尖,比黑漆漆的柜台也高不了多少。
“称一斤红糖!”我甩着嗓子,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缓缓伸出头,还是眯着眼,见我来了,不紧不慢地起身,用大铁勺从糖缸里舀上一勺放在托盘上。记得那时称糖、瓜子、饼干、蜜枣……都是用这样的铁托盘。他看了看准星,顺手又加了一些,旋即又舀下去一点,反反复复,如是几次。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生怕遇到大人们所说的“奸商”,会缺斤少两。说来也可笑,“盯”与“不盯”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那时还不认得秤呢!
只见他从藤椅边翻出一张报纸,先是摊开,把铁盘上的红糖悉数倒在纸上,还用力磕了磕,似乎担心有残留。接着便折出印痕服服帖帖地包起来,是那种好看的规则四棱锥状。男人慢条斯理,游刃有余,看不出他的手竟是那般灵巧。男人用稻草绳捆好,还特意打了个牢实的“结”,稳稳地递到我手里。
记得有次,实在是馋得不得了,回来的路上,我自作聪明地解开了稻草绳,将“五指山”嵌在红糖里,自顾自地将手指头一个个吮吸起来。老红糖粗粝、脆硬,吃在嘴里“嘣嘣”地响。大快朵颐后,却不知道怎么去“还原”,情急之下,只得胡乱地将稻草绳裹在一起。谁想,还没走出三两步,草绳就散开了,红糖撒落一地。我一下瘫坐在地,“哇哇”地大哭起来,怕是免不了父母的一番责骂了。
许是哭声太大,男人竟寻了过来,一把将我拉起。照他的意思,是回小店去——重新给我包上一份。我止住了哭声,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昏黄的灯光映照在台面。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神,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上次光线昏暗的时候,我还偷偷地将手伸向糖缸,许是他两眼昏花,又许是他早已忘了此事……看着我羞赧的脸,他也只是笑笑,心照不宣似的。门外是他嬉戏玩耍的孩子,也成天叫嚷着吃糖,门牙都豁了两个,看上去和我一般大。
拎回来的红糖,母亲小心地把它盛放在陶瓷罐里。包红糖的报纸自然也就归我了。嗬,上面还粘着不少糖粒呢!照例是伸出舌头一股脑儿地将报纸舔得一片潮湿,边边角角也不落下。只在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客的时候,母亲才会做几碗糖水鸡蛋,舀上一两勺红糖,浓稠的糖液洇散在碗里,缓缓地流着。抿上一口,真的!比蜜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