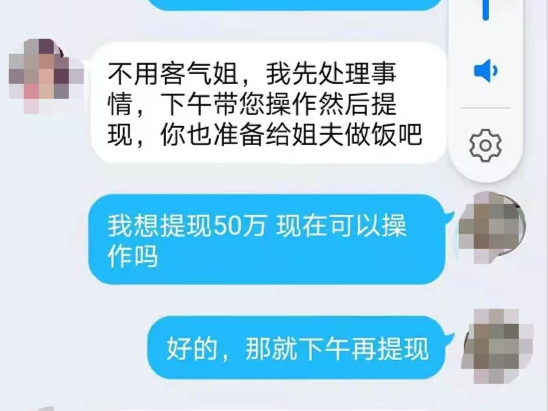每年冬月,乡下二姐总会打来电话:给你灌点香肠,腌几刀咸肉吧。电话这端,毫无例外地欣然应允。
过不久,阳台上,一挂挂香肠、一刀刀咸肉以及几尾风鱼之类,就挂满了。看着这一切,想一位朋友说过那句“把日子过起来”,就暗自发笑。是啊,把日子过起来,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温情脉脉。农历最后一个月又称腊月。有记载:“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岁末年前,囤年货,腌腊肉。待地寒天冻,家人闲坐,灯火亦可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被落实政策后,我全家自乡下搬回县城。记得初冬时节,有位乡亲来访。父亲特意领他到厢房喝茶小坐。厢房的梁上悬挂着一大抱咸货(无外乎咸肉咸鹅之类),特别显眼。客人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就是让他看看,回到县城,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的。那个年代单凭几刀咸肉,几只咸鸡咸鸭,足以佐证在城里生活比乡下不差,往后的日子也滋润。现在想来,这其中自然有父亲的虚荣心理,也可见那时日子的艰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弟妹尚在读书,三个姐姐陆续出嫁,全家5张嘴吃饭,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每日柴米油盐,蔬菜荤菜都要买。不比在乡下,清晨,母亲去菜园,不几分钟总能采回一大挎篮蔬菜。那腊月腌制的咸货,也能吃到来年夏至。中午,炒几碟鲜蔬,蒸几块喷香的咸肉,日子笃笃定定的,不慌不乱。
现如今,吃穿早不是问题,可每到年下总沿袭父辈的习惯,腌制一些腊味。自己也固执地认为这些腊味才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元素。有了这一切,就有了对年的期盼,心里就踏实。
孩子们可不太喜欢吃这些咸货。食品专业博士毕业的儿子和媳妇,曾多次建议我们少吃或不吃。他们哪里懂得,从小盼杀猪,杀鹅,等着这些咸货过年的我们,记忆的味蕾里,早已存储了喷香的腊味,每到年底,我们强大的胃,就会条件反射似的需要填充。一碗白米饭上,铺一层青菜,搛两块咸肉,再挖半勺咸香的油覆至青菜上,感觉扒进口的每一粒米都滑溜溜的,充满了幸福的香气。
小时我随全家下放去的那个小庄村,不过20来户人家。春末,家家都捉来二三十只毛茸茸的小鹅仔回来。鹅儿渐大,早早晚晚的,伙伴们就赶鹅,去野外、去河里。鹅,在吃它的草,在河里嬉戏,我们在一边疯玩:挖老猫,瓦石子,跳房子,拔毛针……玩到天将黑,村口传来呼喊“四丫头、三犟仔……快回来吃饭啰”,才赶紧去鹅堆里,用长竹竿去分自家的鹅。那些鹅,都有各家的记号。或鹅头或身体染上红色,或鹅脚上有记号:什么双脚里丫,左脚内丫,右脚外丫之类。每年我家的鹅,都是双脚外丫,约定俗成的,别家也不重复。鹅很小时,将一只只鹅剪去外掌上的蹼,再用火燎一下伤口,此后鹅的双脚就残缺了两块蹼。如今看来,这做法挺残忍。
腊月一到,那些肥墩墩的鹅们终归逃不过一场宿命。将一只只大白鹅割颈,再用双翅交叉将鹅头反锁绑紧。待一大锅水滚开,倒入摆放在门外的大盆内,将一只只杀好的鹅按入水中,烫,乘热拔毛。然后开膛破肚,洗净,用大盐粒腌。几天后回卤,风干,再几个大太阳,那些咸鹅就晒得干薄薄的,咸香无比。村里一群牧鹅的孩子,此后无所事事。一日日地等待,眼盼着新年的到来。
腊月里,除了杀鸡宰鹅。村里另一项重大活动就是杀猪、吃杀猪饭。谁家杀猪,几乎一个村的人都会涌去。一大铁锅烀出的猪心猪肺猪头肉汤(俗称猪下水),一大脸盆油红发亮的红烧肉,几大水桶盛好的白米饭。大人们坐桌边喝酒猜拳,孩子们端一大海碗,吃着,跑着,闹着。腊月黄天,阳光温暖。家家门前挂着洗晒的各色被条,如彩旗般迎风飘舞。那是一年里最和谐,最美好的光景。
那天回霍山东西溪作家村,见一群人立于一农户门前拍照。走近,见两根长竹竿上挂满了各种腊味咸货。模样虽不雅观,却令人浮想,切一盘蒸透后,它该是怎样的有嚼劲又解馋,禁不住唾津潜溢了。
此刻,又想起那些年的腊味年味。
想起那些再不复现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温暖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