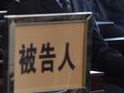针不常用,就要生锈,这是母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这话在她身上得到了验证,她的听力困难已好几年了,许是不常用生了锈的缘故。
搬进小区后,母亲一个人独住四楼。门,进去是关,出来也是关,随进随出随关的还有耳门。常常关闭的耳门生锈了,把所有的声音挡在了外面。没有声音的世界,会不会让母亲怀念曾经的耳朵?母亲说,上了年纪,站哪儿都挡事,再多一对管闲事的耳朵,更遭人嫌。这是母亲在劝慰自己,安慰自己。她最亲近的子女不在身边,在身边的常常是熟悉的外人,当她遇到不便、遇到烦闷、遇到愁苦的时候,只好自己劝慰自己。
在家里呆久了,想去那人多的地方,临出门时,母亲对嘴巴说,我是带着眼睛去看热闹的,你可别乱插嘴!在人群中,母亲坐了下来。通常那凳子,不是有人让出来,就是有人递过来,这样的礼遇,让母亲常常感动。母亲是个沉默的参与者,每个人都知道她耳朵不好,有她不多,无她不少。她像看一部哑剧,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感受大家的喜怒哀乐。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什么,母亲只知道日出日落,昼夜循环。耳门关闭了,心门也渐渐暗合了。人生中很多闹心的事情不是看来的,而是听来的。老来耳不便,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让嘴巴说话,是不给自己麻烦,也不给别人麻烦;是在尊重自己,也在尊重别人,这是听力不济的日子里,母亲思索的结果。很多事情想通了也就释然了。
一棵葱郁的大树,远观是完整的,近看才发现一些暗黑的枝杈老朽了,曾经翠绿的时光永远也不会鲜艳在朽了的树枝上。母亲除了听力不好,视力也在弱化。每周帮母亲拖地的时候,能看到厨房与饭桌下面洁白的磁砖上散落的饭粒、菜屑、头发等。可母亲说,地是干净的。生活的不堪,明明与她朝夕相伴,但她看到的却是清朗的世界。母亲认为自己的眼睛是好的,所以她把听不到的东西交给了眼睛,让眼睛带着耳朵去散步,去看人聊天,去打捞生活的快乐细节。那些漏掉的,或许是一件好事。眼不见,心静,心静方能心安,一个老人的理想生活就是安然地度过晚年。
天作的时候,会来一场风雨;母亲的胳膊作的时候,会伸出另一只胳膊锤打。以痛止痛,是她这一代人纾解病痛常用的方式。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从阁楼上下来,送母亲上楼的梯子,跟母亲开了个玩笑,让母亲踩了个空脚。没钱去医院的母亲,被做乡医的姑父用纱布绑牢了错位的骨头,受伤的骨头,没法报复梯子,只能用痛弥合自己的伤口。母亲在床上一声不吭地躺了四十多天,被绑着的痛熬过一天又一天。
常年为生活劳碌的双脚,已经习惯了踩空踩痛的经历。她不怪脚,也不怪梯子,只怪坑坑洼洼的命运。命运无法选择,她只能面对和容忍。骨头长好了,痛还会时常发作。止痛的膏药贴了一张又一张,指望贴去疼痛,可是贴去了旧痛,又来了新痛,新旧交替的痛的人生,岂能是一张小小的膏药一贴了之?痛的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到了晚年,痛了一辈子的人生不再需要锤打和止痛了,可已是残阳如坠。
大把大把的闲时光,母亲都用来留恋过去。母亲说,年轻的时候,上街下镇来去几十里,风一样轻松,现在这双老腿老是觉得拖不动;母亲说,年轻的时候,她一个人拔几个人栽的秧,现在拖个地都要歇几下;母亲还说,这人老了怎么这么没用!没有经历,就没有这般感慨。人生就像那奔跑的列车,每过一个站台,都会丢下一部分,直到丢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