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视频完整版
大皖新闻讯 “虽然我人在安庆,但户口还在合肥。”从当年的先锋文学作家,到剧作家,影视编剧和导演干出名堂之后,颇有些“他乡日暮故乡弥远”之感的潘军,丁酉年又从北京回到安庆江边筑巢“泊心堂”,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却与四十年前那个错身浙江美院的自己认真重逢。著名文化人潘军日前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大皖徽派栏目,讲述自己的“文化斜杠人生”,潘军从最近自编自导,何冰张国强等人主演的热播剧《分界线》切入,结合新近出版的三卷本画册《泊心堂墨意——潘军画集》,显现出一个“认知高于表现”的手艺人的风貌。手艺人,这是潘军的自我定位。依旧热情似火,依旧犀利先锋,依旧恳切真诚,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个认真的手艺人。
用脸盖个戳做个纪念
人物立起来可以不朽
 徽派访谈直播中
徽派访谈直播中
徽派:《分界线》这部戏播出后口碑非常好,这就要说到潘军老师做导演之前最初的一个身份——作家,实际上这部戏也是根据潘军老师之前的两部中篇小说改编的,是吧?
潘军:对,《犯罪嫌疑人》发在2004年的《人民文学》上,《对门对面》更早一点,发于1997年的《花城》,都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于是就有看过小说的观众问我,为什么过去的小说今天把它拍成电视剧还是那么让人激动,还这么好看?我说,鲁迅先生的阿Q过去这么多年了,却依然还活在我们心中,不是我高比,我的意思很明白——好的人物形象是不朽的;而且,好的故事,好的细节应该也是不朽的。有些故事,比如说《基督山伯爵》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拍,拍了多少版本?人物、故事、细节,如果它具有生命力,你转换一个时代背景,从技术层面讲不是难事,当下无非就是些物理上的变化,但是在人的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
徽派:只要人物立起来了。
潘军:没错,人物必须生动鲜活,具有生命力。小说家出身的编剧,最大的能力,或者说是最大的优势,就是要把人物写好,不能让人物被情节裹挟着走。当然,这两部中篇小说合并,从题材上是有共通的一面的,比如说都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起伏,命运跌宕;比如说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是送水的,一个是开出租车的;比如说都是因为经济困扰而离异,我把他们构成师徒关系,非常合适。把这两部小说的人物关系重新纠葛起来,衍生开来,对我来讲不是难事。
 《分界线》宣传海报
《分界线》宣传海报
徽派:小说是您自己写的,然后您自己来编剧,然后又是您自己来导演的,其实你也参与了表演。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潘老师之前编导过《5号特工组》等,每部戏您都会露个脸,客串一个角色,比如戴笠。
潘军:拍《5号特工组》,本来是请了一个演员演戴笠的,但是他把戴笠演的很概念,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就告诉他,虽然你认为戴笠是个反面人物,但是你不能演得很脸谱化,你还是要当一个人物来演。可是怎么讲他就演不好,而且那个时候都已经开机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试试。结果这一试,我自己连演了三部戏的戴笠——从《5号特工组》到《海狼行动》再到《惊天阴谋》,这三部戏现在被人概括起来叫做潘军的“谍战三部曲”。最搞笑的是还有其他剧组,不知道我是谁,制片人跟导演说,你找《5号特工组》演戴笠那个人演,演的阴得很,于是演员统筹就打电话来了,说潘老师最近我们有个戏,中间戴笠的戏份还很重,能不能帮忙来演一下?好像我成了专门演戴笠的演员。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还以为您是表演科班出身的吧?
潘军:我只是在我的戏中间露个脸串一个角色,但不会到别的戏里面去串,已故的导演何群拍《茶馆》的时候,希望我去演个崔先生我都婉言谢绝了。
徽派:是不是也有向希区柯克致敬的意思。
潘军:他只是露脸,没有戏份,甚至没有一句台词,就露个脸,或是挤公交车被人推下来,没挤上去,或是在旋转门中间转了半天出不来,他总是这样带点滑稽。我露一个脸有点像书画家,写毕一幅字画,在上面盖个章,经年累月这个画面受损了,那章还在是吧?就是有个纪念意思,我用脸盖了一个戳。
我是个容易被点燃的人
也是个内心有定力的人

徽派:最近的“黄山书会”上潘老师再现咱们说的斜杠人生,我好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
潘军:我打小就喜欢画画。或许因为家境影响——我父亲是编剧,母亲是黄梅戏演员,对艺术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我又是一个容易被这种兴趣点燃的人。我后来总结自己学画,可能是某一天放学的时候,看到外地的一个画家在河边写生,觉得有意思,别的孩子都回家吃饭去了,我却情不自禁停在写生人的后面,等他画完我才回家。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把我的绘画梦想点燃了呢?还有,当时文化馆的老师经常到剧场画舞台速写,这个对我也有刺激。我临摹过很多连环画,插队的时候,不出工的时候我就背着写生夹四处游走,我把周围村子的村民几乎都画下来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当时报考的是浙江美术学院,参加了复试,身体也体检了,但还是落榜了。我私下里琢磨,那一年高考很在乎政审,那时候我父亲还是右派,会是这个原因吗?我觉得自己画得不错啊!第二年我就改考了文科,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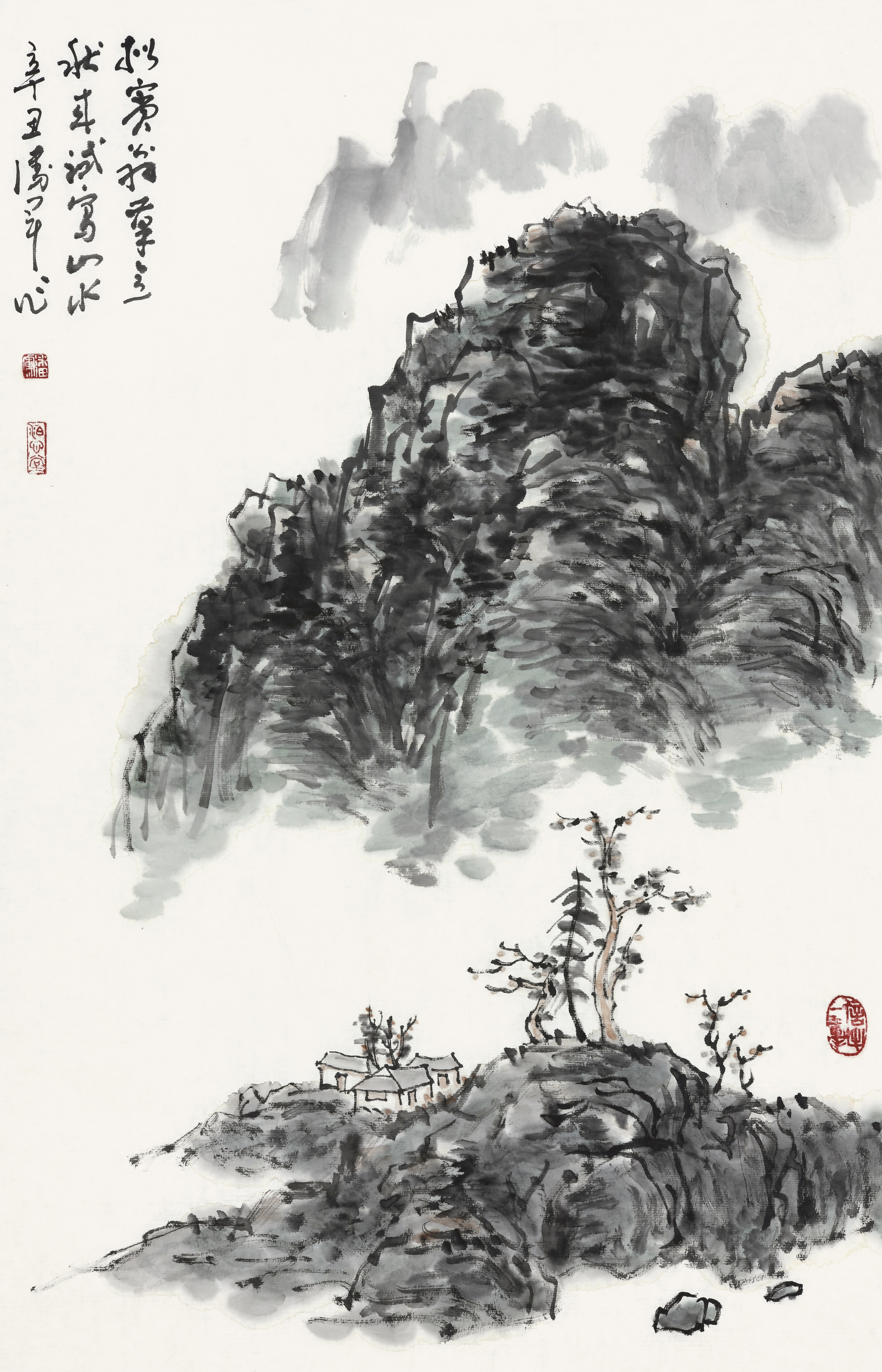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完全是自学的吗?
潘军:完全自学,没有拜过师。就像我后来做导演一样——我就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谢晋导演《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剧本,像会计的表格一样看不明白,但是我爱琢磨,居然就把它读懂了,既然读懂了,那就可以试试。我靠的是一个悟,和一份热情。等你有了这种悟以后,你会意识到自己哪方面的不足、不够,需要补课。比如说,画素描的时候,人体结构不是很准,那我就要找一些人体解剖的书看一看,看骨骼肌肉的分布,肌肉的变化,把这个搞准确了,我再回头去画石膏就踏实,肯定画得就比原来好了,还是得靠自己去琢磨。
徽派:自学成才。
潘军:自学是事实,成不成才不重要,觉得开心就好。这回安徽美术出版社推出《泊心堂墨意——潘军画集》,分了人物、山水、戏曲人物和花鸟、扇面三卷,很沉重的一套书,我那天试了一下,足有20斤!这套书对我来讲是个人绘画的一次总结,更是一个纪念。很多朋友也多少有些惊讶,他们总以为我小说的影响大。实际上从国际层面上讲,我的戏剧比我的小说影响要大,比如说我的话剧《合同婚姻》,北京人艺首演,一直演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个版本。然后美国华盛顿DC的一个华人话剧团也演了。再后来又在意大利米兰戏剧节演过。那不勒斯大学戏剧学院还要把《合同婚姻》收入教材,为此意大利大使馆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再说《霸王歌行》,根据我的小说《重瞳》改的,《重瞳》那年位居中国当代小说排行榜榜首,影响比较大,至今为人谈论。后来我把它改成话剧,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的,那个戏演的地方就更多,至少十几个国家。《霸王歌行》后来是获得了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的优秀剧目奖。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王晓鹰导演的。
潘军:是晓鹰导的,他很棒,这个奖很不容易,毕竟是世界戏剧节。
徽派:这就是刚才说的,只要人物立住了立起来了,他可能不仅能穿越时间,空间、民族也不是问题。
潘军:同意。北京人艺首演《合同婚姻》第一版,当时导演是前不久刚去世的人艺的院长任鸣,是我和王晓鹰共同的朋友,我是从晓鹰的微信里得知这个噩耗的,很悲痛!记得每晚演出之后,任鸣都会邀请几位嘉宾,比如邹静之、刘恒、解玺璋等,然后把观众留下来座谈,和主创人员互动。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美国观众,能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他说这个戏如果到美国去演也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个故事他感觉到很亲切,剧中的人物好像都是他的一些朋友,这让他很惊讶,想不到中美双方在这方面怎么这么默契?剧中的情节,美国人也会这么做。我想,这就是带有一种共性。人类的共性。所以说,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或者影视剧,只要形象有分量立住了,显示的就是生命力,就怕你写的不好,很苍白,那自然不行。
徽派: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戏,可能会故意强化这种文化冲突,但实际上您只要沉浸在普通的生活里边,大家的感受认识其实也都是相通的,很多情感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潘军:我们再说回《分界线》,现在收视率很好,反响一直都很强烈,但是任何一个作品出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某些段落节奏有点慢,比如说这个孩子病了,医生救护怎么拍得那么细致?警察到案发现场需要拍得那么具体吗?我非常理解。当时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在剧组会议上提的要求就这么两点,第一,要拍一个让大家感觉到亲切的故事,感觉到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这是我的一个诉求,用现在的话就是要接地气。第二,我认为最大的艺术感染力是身临其境——要让观众走进这个故事,能代入,观众会感觉自己就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旁观者,这种逼近是有考量的。但别的导演可能不会这么做。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自觉一直是一个有内心定力的人,创作者不要去取悦什么人,更不能迎合。无论你是写作、画画还是写戏,拍戏,你没有内心的定力,做事是很茫然的。我甚至可以讲得绝对一点,有些东西,比如说画,比如说小说,可能就是给一个特定的人群看的,就像这部小说,100个读者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喜欢,看懂了,喜欢了,那就是写给他们看的,另外98个人不重要了。但有些东西恰恰相反,比如说电视剧,你必须要面对大众,你不能让大家感觉这个故事很乏味,那样人家就不愿意看了,立即换台。所以做给谁看,对创作者又是一种定力。
 “我自觉是一个内心有定力的人”
“我自觉是一个内心有定力的人”
徽派:要有一个坚守的东西在。
潘军:必须的。我给小众的,那就给小众。比如说一幅书法作品,大众说这是丑书,完全不必当真。你若当真那就是失败。创作者内心的定力应该是永远保持,千万不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最后一辈子下来就是非牛非马,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堆,画了一大堆,什么都站不住,什么都没有价值,这才是最大的遗憾。那天在画册的发布会上,有人问我,潘老师你怎么突然画画了?我说不突然,绘画对我而言是圆一个梦。从时间轴上来看,我在写小说之前就画了,只是后来我调整了时间,把画画迟滞到了今天。
舞文弄墨泊心存高远
不求圆满见得人高明
 徽派直播访谈现场
徽派直播访谈现场
徽派:你说绘画是你最后的精神家园。
潘军:我以前说过这个话,我这一生概括起来就四个字——舞文弄墨。60岁之前,舞文;60岁以后,弄墨。60岁对我也是一条分界线。于是60岁那年,我开着车长途奔袭了1200多公里回到故乡安庆,在长江边上重新买了一个房子,取斋号:泊心堂。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份安静,一份安逸,一份不被打扰,这都是享受,都是奢侈。回家这几年过得很逍遥,很安逸,就在于心静下来,专心致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对我来说,这就是个一份美好,就是诗意。我这个人有个信条,广交朋友,不混圈子。在圈子里面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我也不喜欢一嘴毛的事,成天忙忙碌碌,其实内心很空洞。
徽派:您强调的是自己内心的那种圆满吗?
潘军:谈不上什么圆满,个人信条而已。实际上人并不复杂,大家都是明白人,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了点亏都很清楚,区别在于说与不说,忍与不忍。你自己做事,你高兴不高兴,你自己最清楚。我在画册的序言中也讲了,一个人要由衷地看到别人的好,不是敷衍,也不是奉承;更要由衷的认识到自己的不好,你不可能是完人,你总有不好的地方。你自己是不是心里有数?你是不是要做一个有数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自觉离自己设定的目标差距很大。就拿绘画来说吧,中国水墨画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妙就妙在它的偶然性,它有很多机缘,除了笔墨纸砚合适,心情合适,甚至都可能天气合适,都可能导致一部作品的成色高下。只有画画的人,他才有这种感悟。我画《霸王别姬》,当时就有了一种意外的欣喜,后来有人出钱要买,价格还不菲,但我不卖。不卖的理由是我无法保证我能否再画出更好的。我跟我女儿潘萌讲,将来我留下的一些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卖,我委托你捐给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博物馆艺术馆,等你们的后人去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在某一个博物馆与他外公的作品邂逅相遇,那是多大的欢乐?文化应该属于全人类。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潘军:人还是得有点理想。如果这个世界简单到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摆平,这个世界就不好玩了,就没有一点意思了,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意味了,甚至太悲哀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有点精神层面的东西。
徽派: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其实您很悲观,说离自己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您说的目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能不能简单描绘。
潘军:比如,我至今没有拍成我想拍的电影。我对影视导演方面的琢磨是很透的,我上大学在安大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前苏联导演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比砖头还厚。
徽派:为什么会专门借那本书呢?
潘军:这就是一种直觉,觉得这本书很好玩,图文并茂,很多剧照,很多的导演画的一种现场的机位图,看了入迷了以后,然后用一个大本子就把它从头到尾抄下来了,这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的,几年以后这书才再版。我看过不少片子,现在跟那些从电影学院出来的人谈电影,很多时候他们是接不上话的,我看过的他们没看过,都看过的他们没有我这样的认知。我一直就我想拍的几部电影,比如《重瞳》,比如《草桥的杏》。我对标的作品是黑泽明和阿巴斯,我有这个底气,但是我没有一个平台,一个创作环境,很无奈。前几天,香港得奥斯卡摄影奖的摄影师鲍德熹,看过《隐入尘烟》,跟我在微信聊天,说当年如果我们把《草桥的信》拍了,哪还有什么《隐入尘烟》呢?昨天和几个朋友聊天,从《分界线》谈起,有人就提议要我把合肥的张家四姐妹拍个电影,我说这个题材我早就想做,我也有能力把它做得好。现在你们回答一个问题,给不给做?报批需要程序,但凡程序都是一个双刃剑,既能防止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可能会无意中伤害一些好的东西,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尺度为标准?
手艺人的观点
认知高于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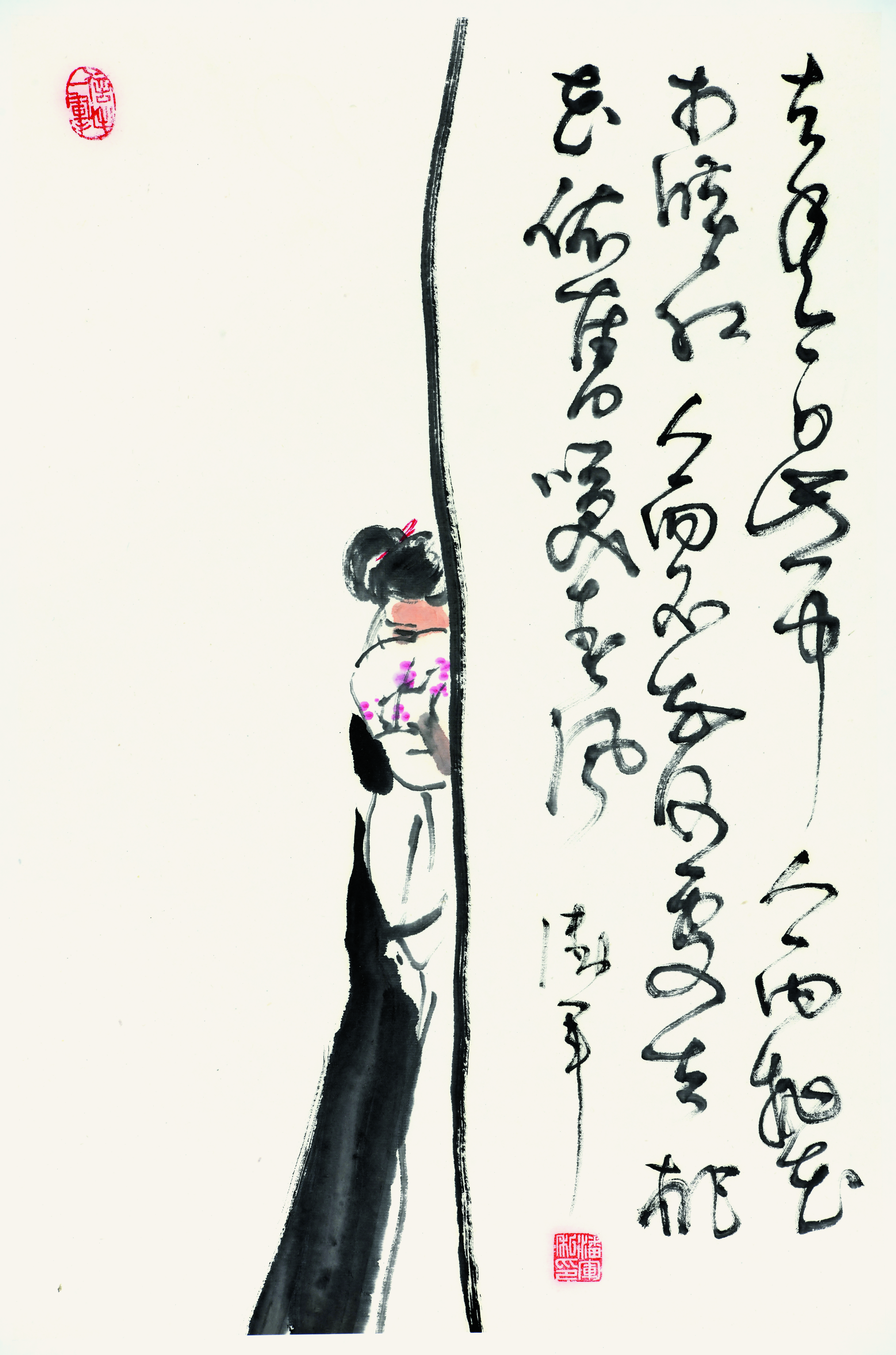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您自我定位为“手艺人”,能具体谈谈吗?
潘军:手艺人其实是很享受的。通过自己的手,一个木匠可以把一根木头变成一把椅子,一个石匠能将一块石头变成一尊佛像,这是很快乐的事。但凡做出绝活,随即怦然心动!比如某天我画出了一张特别得意的画。这种心动,是建立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对自己来讲,我可能这辈子再也画不出来了,它有偶然性,有运气因素;第二个是在横向的比较上,拿出去跟那些最牛的作品比较,一点不惧。关于书画,我有一个观点,用一句话说就是:认知高于表现。
徽派:认知高于表现!最后比的还是境界和沉淀。
潘军:很多书画家,笔墨技巧已经很成熟,但是为什么老是出不了好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认知不够。举一个例子,我画过一幅画叫《人面桃花》——这个题材应该不新鲜,上网一搜,无非是公子作揖、小姐羞涩之类。但是我这幅的构图却以一条线平分画面,右边用行草抄录了崔护的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左边寥寥几笔画了一个以一把桃花扇半遮面的姑娘,身披黑斗篷。这幅画作完我就很激动,为什么激动?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好的视角,我把我和写这首诗的崔护化为同一个人了,我的字就是崔护题到墙上的字,崔护看到的女人就是我看到的女人,我是等于站在姑娘的对立面来作这幅画的。用摄影的语言来讲,我用的是一个主观镜头,是我在看她的镜头,这个创意对我来讲就是石破天惊——还是认知成为关键。
徽派:纯粹只有技巧还是不够的。
潘军: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画八大山人。以前看了很多用国画用油画表现八大山人的画,我都觉得不足,因为都是参照历史上传下的那一幅线描石刻,八大山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朱耷是一个贵胄,有皇家血脉,一个遗民活在别人的时代,骨子里是不服不甘的。这种不服不甘,一定会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候,比如说在深山里,发泄出来的!所以我要画的,就是要表现他骨子里的这种不服不甘。他笔下的鸟为什么老是要白眼看世界呢?那应该是对这个世界不喜欢。你觉得他没有这个认知吗?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认知是牵强附会吗?我认为不是,如果这是他的明朝世界,你觉得他会翻白眼吗?不会的。
徽派:通过他自己的眼神和他笔下的鸟的眼神来表达。
潘军:对。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腔调,应该与认知有关,所以我才坚定地认为:认知是高于表现。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所以说潘老师的艺术人生其实确实是一个圆。刚才潘老师说了自己不愿意卖《霸王别姬》,让我再次想起小说《重瞳》,项羽在您笔下成了一个诗人,而不是大家后来更多人理解的一个失败的英雄。咱们再往前一直回到您最早写先锋小说的时候,现在回头来看,其实现在我觉得您看八大山人或者您对崔护的理解,观念上还是很先锋的,这应该是一种传承或者连接。
潘军:所谓的先锋是一种探索精神,当然不会局限于文学。所以我很感谢当年浙江美院没要我,如果我被录取,对我来讲人生至少没有这么丰富。我甚至敢断言,既是是画,也未必能画得过现在的我。因为你的认知太单薄了,你除了临几张画,学点常识以外,你还能有什么作为?这是成就不了一个画家的梦想的。你看看黄宾虹的谈画录,多大的学识,多大的悟性!黄宾虹如果没有这么样的分量,像傅雷这种清高傲慢的人,怎么可能对他恭敬有加?有时候,我很感谢上天赋予我的这一种人生计划,这就像打牌一样,我可能起了一手烂牌,但我自觉打得还不错,就当吹牛吧。当初我离开机关的时候,有人就以为我这辈子玩砸了,我毫不理会。机关对有些人合适,但对我不合适。我不喜欢那种假模假式,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手艺人好。没有多少打扰,让我专心致志的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做事要有一个匠人精神,你沉浸其中,就是一种享受,即使是苦中作乐。
最公平的不是时代喧嚣
时间证明你行你才真行
 潘军为徽派题字
潘军为徽派题字
徽派:我想引入一个话题,就是您先从先锋文学写作开始,一直到后来,其实您一直都没有加入中国作协是吧?
潘军:对。
徽派:这是您的一个选择?
潘军:前面说了,我不是一个喜欢混圈子的人,放大一点,我不参加任何协会。最近花城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上下卷的创作随想录,书名就叫《一意孤行》。我喜欢一意孤行,不喜欢扎堆。再有,加入协会或者担任某个职务,能让你写得更好还是画得更好?我也不要任何职称,更不会申报任何奖项。但我有野心,希望能拥有厚重的作品,我就要这个。
徽派:您还是比较认可自己,您刚才对自己的评价,觉得自己是一个手艺人。
潘军:每个人写作的人都可以叫作家,画画的人都可以叫画家,所谓的“家”难道是什么荣誉吗?画家跟画画的人不能相等吗?作家跟写作的人不成比例吗?难道称你作者称我是作家,就觉得我比你高明一点?完全不是!我比你高明的可能就是我的书写得比你好,这个是真正的高明。你的高明在于你的画比我的好。同样是电视剧,我收视率比你高,这个是硬的,没有办法谁也帮不了你。但这个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尺度,不能以此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最公平的是什么东西?最公平的是时间。鲁迅不加入任何组织不得任何奖,但他的作品生命力最强。多少年前日本的一个汉学家在北京采访我,问你对鲁迅怎么评价?我说我有一句自以为经典的话——鲁迅和中国作家,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作家是个什么关系?是一枚感叹号的关系——鲁迅是一点,我们排成一条线,一点和一条线之间的距离,永远不可能填起来。鲁迅是唯一的。不服不行,别人说你行也未必行,自己说自己行就更不行,时间说行那才是真行。
 潘军画作
潘军画作
徽派:这段是贯口吗?好,咱们换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我记得以前采访您的时候,您在您女儿很小的时候,您就和他一起写过一本书是吧对,然后后来潘萌他在美国是学……
潘军:潘萌14岁的时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套叫“两代人丛书”,我印象中,有我和潘萌、舒婷和她的儿子,还有叶兆言和他的女儿。这是本合集,她选她的我选我的。几年以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潘萌就写了她的第一部长篇《时光转角处的二十六瞥》,由《花城》《作家》和《芙蓉》三个刊物同期推出。后来出单行本的时候,出版社让我来写个序,潘萌就拒绝了,说我是你女儿,你怎么说都不合适。我说你想请谁来写?她说想让史铁生叔叔写。于是我就去北京史铁生家里,说孩子出书,想请你写个序。史铁生跟我讲,我几年前就公开说我不再写序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孩子是个例外。他很快就把潘萌的书稿读了,写了序文《不拘一格的想象力》,这让我很感动。
徽派:潘萌现在在洛杉矶?
潘军:是的,她学的是编剧硕士,然后又学这个制片,那一年随美国电影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后来又在环球电影公司实习。现在她已经定居洛杉矶,有一个合伙人的电影制作公司,同时兼任《环球银幕》驻北美地区的记者,采访了不少世界电影的大腕。他们的公司最近刚刚拍了一部院线电影,中文翻译过来叫《孤星人》,中国、美国、意大利、墨西哥合拍,男主角就是那年的奥斯卡《罗马》的男主角,刚在纽约和洛杉矶举办了首映式。
徽派:我想问的是潘萌学了她的专业以后,因为您现在也经常从事影视剧这方面了,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之前你对他的帮助可能稍微大一点,现在她也会给你一个反哺。
潘军:我觉得我俩现在应该更像是专业上的朋友,畅所欲言,而且就一个问题谈得很有深度,见解基本上一致,但趣味有别。
徽派:良师益友了。
潘军:她在视野上比我宽阔,阅读面比我大。她懂英文,能看到很多英文的书和原版电影,遇见优秀作品,会及时推荐过我。而且,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潘萌在思想的那种锐气,包括有一种艺术敏感性,还是比我们这些人要强,这个也是不服不行。我为她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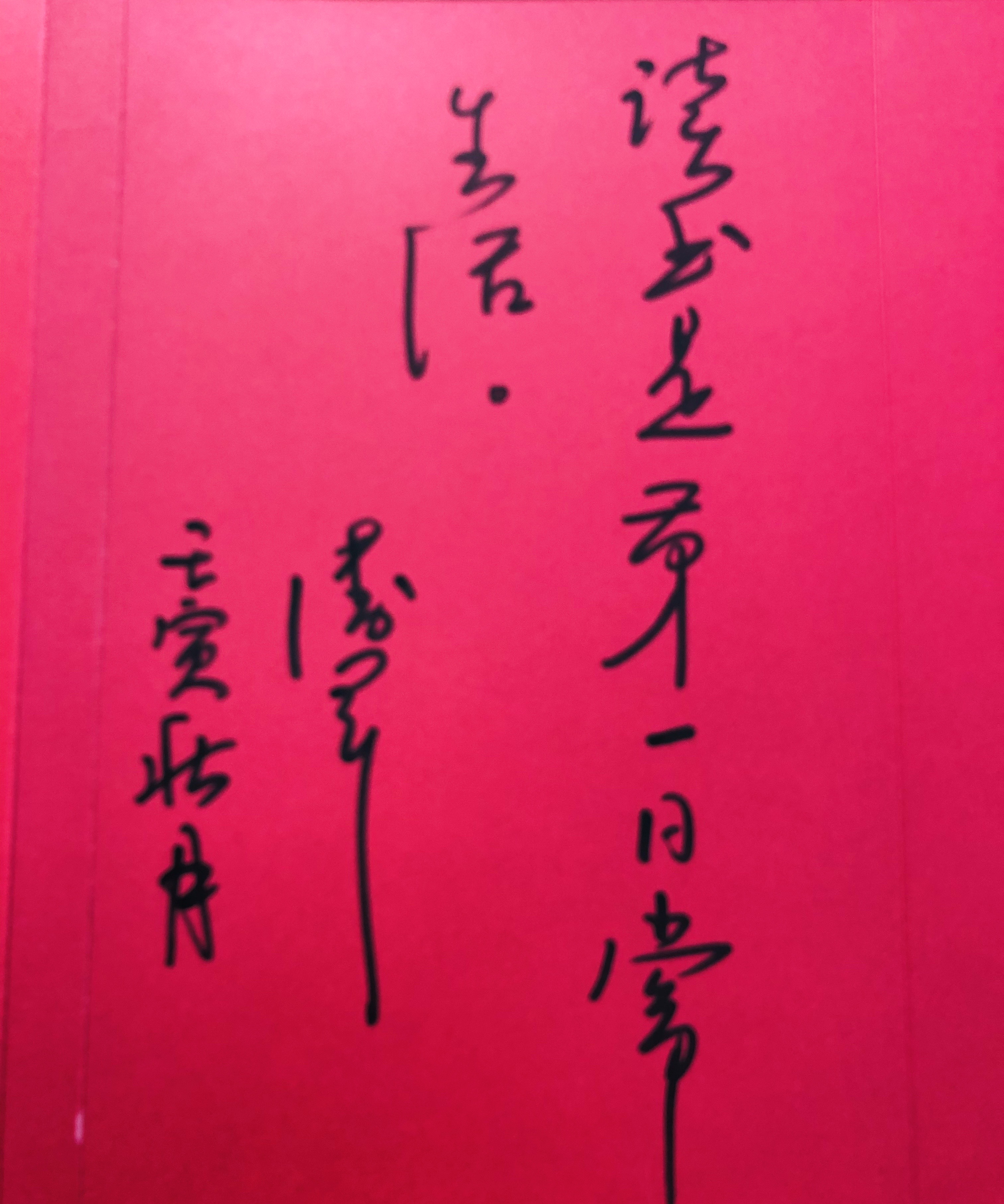 潘军徽派题字
潘军徽派题字
【潘军谈安徽文化】——
带着正确的认知耕耘有营养的土壤
合肥这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当然,我指的是经济的、外在的、看得见的。安徽的历史文化上确实很辉煌,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配得上文化强省,但俱往矣。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安徽的文化,这个我实际上没有发言权,因为我阅读的安徽作家的作品很少,看的画和片子也少。所以我只能从个人的感慨上说点想法。
第一,这块土壤应该出现一种很辉煌的文化气息,因为这块土壤是有营养的,它应该能出现璀璨的文化氛围,不能荒废。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第二,我们现在主张做文化,我觉得应该从两个维度上去思考。其一,有些项目确实要靠政府的支持,推动。但要判断什么东西值得推?应景的东西不要推,推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按专业要求,集中精力推出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因为这样的项目靠个人是办不了的,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张家四姐妹。其二,作为专业人,你永远要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够?什么叫不够?你不能说我出了很多书——我在安徽作家中出的书应该是最多的,但多不等于好。就像当年《棋王》面世,只是一个中篇小说,我觉得那就是好。不管作家画家,自我的判断力和认知力都不能脱离这个维度,你永远是最懂自己的人,别装,别演,认真琢磨,埋头去做。 大皖新闻记者 蒋楠楠










